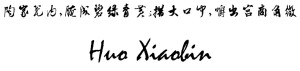大主教因特殊需要,授命迈克尔海顿(Michael Haydn)为小提琴和男高音写几首二重奏,但当时迈克尔生了一场大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工作。于是大主教威胁要扣他的薪水。莫扎特听说了迈克尔的困难,便立刻开始工作,他每天都去探望海顿,在他的床边创作。不久二重奏(K423,424)就完成了,署上海顿的名字交给了大主教。
——匿名
自从2011年夏天我遭遇了人生之中最大的变故和磨难,至今已经是两年了,客观地说,我还未从这次劫数中完全恢复过来,只能说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慢慢地成长,成熟和重新开始。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的磨难降临在我的心智最有抵抗力的时候,最终没有把我打到,反而让我从中学会了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有的担当,责任感和对在这个时候依旧停留在我身边的幸福的珍惜。
我在去年六月回到了家,辗转数日,又回到了北京找了份工作,攒点钱为自己以后的打算作准备,也是那个时候,我又见到了阔别许久的高兄,因为他的工作是咨询,所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出差,我便在他租的小房间里住了下来,本来是打算暂住一段时间的,但是没想到,一住就是一年,直到我又要离开中国的那一天。
粗略算算,这一年我们相见的次数也并不多,每当高兄回北京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做饭吃,一起到附近的月坛公园散步,谈谈心,有时候会买两瓶啤酒,过过酒瘾。就这样,一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如果在五年前的话,我不会觉得一年有什么可惜的,但是现在的我,心境早已和那时不一样了,一年的逝去,意味着我离死亡又近了一年,意味着上帝留给我的时间又少了一年。
但是,我这一年过地其实是蛮充实的,这两年我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要试图靠别人,只有自己亲手创造的人生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我靠自己的工作攒了去欧洲的钱,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以后如果还想去读法学院,我依旧会先通过努力工作攒学费,而不会再试图依靠父母或者其他人。甚至在工作之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依旧能找回曾经拥有过的那种闲适和情调,打开莫扎特的音乐,带上那架陪伴了我快十年的“老骥伏枥”的耳机,沉浸在莫扎特暂时给我带来的安宁和欣慰之中,久久不愿意醒来。为此,我去年竟然还能重新开始《莫扎特笔记》的写作,而现在——正如这些文字所显示的——我依旧在为莫扎特的音乐写字幕。(A)
我接触莫扎特1783年为小提琴和中提琴写了两首二重奏其实也并不是太久的事情,应该是三年前吧,那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也喜欢莫扎特,她的生日是在过年期间的某一天。我在想给她送什么样的礼物,在绞尽脑汁想出了两首词之后,忽然想到送她一张莫扎特的唱片,我于是又到中关村图书大厦——那是我最后一次去这个书店——挑CD,最后选了一套我还没有听过的PHILIPS的DUO系列,这里面收录了莫扎特为弦乐二重奏和三重奏写的音乐。后来我就没有仔细听过这些弦乐二重奏了,因为我本人对纯弦乐作品不是太喜欢,直到一周前——这个时候离那个女孩离我而去都已经快两年了——当我看到了莫扎特和米歇尔•海顿的故事的时候,怀古思今,想到现在只有高兄这么一个旧人还没有抛弃我,把我当作朋友,不禁眼角开始湿润了,但是一个男人哪能这么容易哭呢,于是找出了莫扎特和米歇尔•海顿友谊的见证:小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K423和K424,这也是我三年来第一次细致地聆听这两首弦乐作品。
莫扎特的这两首很特别的二重奏的出生也算是歪打正着,如果没有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好友海顿,恐怕我们今天也不会听到它们了。注意,这个海顿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海顿,而是后者的弟弟,全名约翰•米歇尔•海顿(Johann Michael Haydn)。在当时来说,这位海顿和他的哥哥约瑟夫•海顿也都算是乐坛风云人物,也都在贵族那里有一份糊口的工作:约瑟夫•海顿在埃斯特哈齐亲王那里工作,而米歇尔•海顿则从1762年开始被萨尔茨堡大主教收入门下,成为大主教克罗莱多(Count Hieronymus von Colloredo)的兔宝宝(御用音乐家)。从此,这位海顿便和莫扎特父子成为了朋友,尤其是莫扎特,后来莫扎特从萨尔茨堡出走之后,还常常替这位酒鬼朋友分担来自苛刻的大主教的压力和痛苦,这两首弦乐二重奏就是他们的纯洁友谊的明证。
从这两首二重奏的编号K423 (G大调)和K424 (B大调)就能看出,莫扎特写它们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大主教的人了,而是一个在维也纳自力更生的快乐的自由作曲家,而他的多年好友海顿老哥却还呆大主教的宫廷里,视野日渐局限,生活无聊乏味,关键是还要看脾性独特的大主教的眼色,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当莫扎特知悉老朋友的窘境的时候,心中的那些任侠好勇,拔刀相助的义气自然油然而生,情愿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乐呵呵地来帮海顿一个大忙。对于莫扎特来说,这不是他的工作,所以不像海顿,创作的时候毫无压力,这种激动之中渗透着博爱,情义之中饱含着自信的情调,在第一首二重奏之中表现地非常明显,而在第二首之中,莫扎特似乎更能从纯粹作曲家的角度创作,显得更加平和,风格更加室内乐化。
究竟是那档子事需要两个乐坛高手来应付呢?原来那时米歇尔•海顿的东家(莫扎特的老东家)萨尔茨堡大主教规定期限要他写出6组小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但是海顿当时身染疾病(我推测是酗酒所致),故写了四首之后,就死活写不出来了,莫扎特表示愿意提他把剩下的任务完成,虽然他是很讨厌自己的老东家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莫扎特还是萨尔茨堡的音乐家的时候,他都已经不想为克罗莱多写什么音乐了,而这个时候,他作为一名自由作曲家,却又要为这个傲慢的男人作曲,心中的纠结要有多大,当然,最终两首二重奏还是诞生了,尽管第一首和第二首相比是很情绪化的,仍旧不失和谐和美妙,据说,最后这六首二重奏在大主教宫廷里被演奏的时候,大主教并没有听出其中有两首是其他人代笔的,我想他压根就没有仔细听任何一首。(B)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中间,高兄突然回来了,所以我就暂时把它放下了,我们又像以前那样一起做饭,一起到月坛公园散步,聊天。我们第二天中午炒了一个韭菜,然后拌着面条吃,高兄问我还记不记得杜甫有一首诗就是写韭菜的,我于是查了查,原来他说的就是那首著名的《赠卫八处士》,虽然我以前读过,但是显然那时没有什么感觉,只依稀记得前两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但是高兄说他高中的时候都背过这首诗,今日再读,依旧忍不住快要落泪。
我又重读了一遍这首诗,才发现现在的我读的时候,和高中时候的我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对杜甫被贬之后,忽然发现一个老朋友对他殷勤款待的感觉是没有任何概念的,而现在我差不多能够体会到杜甫写这首诗的那种欣慰而又悲凉的心境了。一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一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已经让我心有戚戚焉,马上便想起了这几年自己的遭遇,想起了莫扎特和海顿老兄的故事。或许这个世界上令人感动的三样感情:亲情,友情,爱情中,唯独友情是最弥足珍贵的。亲情之大,重在血缘,即使你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兄姊,仍旧不能对其弃之不顾,因为他们和你是血脉相连的;爱情之美,重在吸引,倘若某一方对另一方已经没有价值了,很容易就劳燕分飞,自古女子皆“心如鸟兽,难养易畔”,此言不虚也!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够在你是个落水狗的时候,不会离开你,不会搬起石头去砸你,而是会伸出一只手,把你拽上来。当你气宇轩昂,志得意满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聚集到你的身边,这些人可能会包括温柔漂亮的女友,口若悬河的朋友,这时你的心态会像中国的楼市一样都是泡沫,一旦这个泡沫破灭了,那些惟愿给你锦上添花的男男女女便瞬间消失地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给你雪中送炭,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仅仅是因为你在大浪淘沙之后,知道了谁才是你生命中真正愿意帮助你,关心你的人,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磨难,这些人的仗义你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
所以说,海顿老兄是幸运的,杜甫是幸运的,我也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是中了大奖的那种幸运,而是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的幸运,是在你挺过了完全可以把你摧毁了的苦难之后品尝到的幸运,是你看淡了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之后从已经变得清澈无比的瞳孔中窥视到的一根幸福之羽。(C)
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苏东坡的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萌的政客,最可爱的吃货,苏东坡就是靠的这种心态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他和自己的弟弟苏辙的情谊也是今古佳话,他们两与其说是亲兄弟,倒更像是患难知交,在两人遭遇人生磨难的时候,想必互相和过不少诗,聊以释怀,这点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比不了了。王安石罢相之后,只能一个人骑着小毛驴乱转,好像神经都不正常了,老看见因他而死的人;而迂叟醋老官场失意了,就一个人躲到洛阳不出来,写了十五年的书,颇有我们山西人耐得住寂寞的执拗,恐怕我也会像他那样,靠一张“铁屁股”,冷板凳一坐就不起,花数十年的时间写《政府论》了。当然,我都没有机会官场失意,因为我的政治理念实在太保守了,竟然和司马光一模一样,和如今的政治理念实在格格不入,所以我压根连现在的官场都不会考虑进,直接就自令见放了,和司马老比起来,我似乎更加悲壮。不知道自己晚年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像司马光一样,临死之前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即使几个月也可以。毕竟,我作为士大夫的后人,又以士人自居,倘若今生不能“居庙堂之高”一回,肯定死不瞑目,下辈子也不会选作北冰洋的海豚了,而是选择继续投胎为人。
当然,小酌之后,“发思古之幽情”,“独怅然而涕下”,就像文人骚客的每日功课一样,完了之后,该干嘛还得干嘛,就算司马光一个人在洛阳,不也得吃饭睡觉吗?所以,还是人家苏轼坦荡,虽然被流放了,但是到一地,爱一地,爱一地,吃一地,今天还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明日便“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了。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如我和高兄一样,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最主要的日程就是“今天吃什么呢?”,虽然吃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是生活还是不能没有吃的,吃得好,才有基础去吟诗作对,去拈花惹草,去出将入相,“自道平生为口忙”,作为一个一年长了十四斤的初级吃货,我对这句座右铭表示赞同。(D)
我有一本一个德国人写的莫扎特传记,里面有一副插图,至今记忆犹新。莫扎特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在晚间的烛光下,一个人坐在一只烧鸡前面,拿起了刀叉,吃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本来很平常的一幕,为什么如此地让我眼角战抖,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在想:“真希望有个老朋友坐在对面,一起分享这桌美食和美酒。”
我在这两年之中成长的一个方面便是体会到了分享的乐趣,曾经的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但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无常百态,我体会到了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的幸福,这种幸福也是双向的,我在遭遇了欺骗,背叛和抛弃之后,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私,无情,而是变得更加无私和懂得奉献,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对我真正的朋友和亲人。也是因为这种成长,我才会体会到了莫扎特的两首弦乐二重奏中的那份友情的见证。这两首曲子并不是独立的,正如它们的编号所暗示的,它们不仅仅在创作时间上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情感维度和发展上也算是难兄难弟,恰如他和海顿的友谊一样。如果说K423像是莫扎特和海顿见了面之后激动而又坦诚的促膝长谈的话,K424就像两人平静下来之后,班荆道故,一起到萨尔茨河边散步,回忆曾经共事的光阴,感叹年华老去,甫见即别的情景。K423的第一乐章中的小提琴声部明显要比中提亲声部激动和慷慨,好似路见不平的莫扎特替海顿诉说出来对大主教的不满,而中提琴就是任劳任怨的海顿,面对小提琴凌厉的气势,虽然连连答应,却又非常无奈,人生就是如此,有何办法?简短的第二乐章中,莫扎特平静下来了,道出了对故交的无比同情,然后在第三乐章两人开始商量由莫扎特替海顿分担一些工作,虽然小提琴已经不再是像第一乐章时那样盛气凌人,但是仍旧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中提琴仍旧像是生病的海顿,作为辅助的乐器,和小提琴完成了一个充满自信的结尾。
第二首二重奏就不像第一首那样情感张力如此地紧凑,它一开始的情绪就让我想起了贝多芬的E-flat大调三重奏(Op 70 No.2)。第一乐章采用了简短的慢板+快板的海顿(就是我们熟知的海顿)交响曲做法,这个乐章中的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对比不再像前一首那么强烈,而是被赋予了更加平等的地位,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莫扎特义愤填膺地写完了第一首,该发泄的都已经发泄了,现在才在写一首纯粹的音乐,即使不是纯粹,也是在写他和海顿老兄的友情,而不是抒发对大主教的不满。之后的乐章的速度标记是“如歌的行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感情线却很长,似乎它承载了许多的回忆,而下一乐章“主题和变奏”则在前一乐章的情感的有节制的抒发之后,转为叙事,在主题和6个变奏之中,人生与君共处之岁月历历在目,“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虽然有些许感伤,但是能够重逢已算人生之美事了,有什么理由不更加振作,更加自信呢?Stand Up Guys!(B)
的确,我也站起来了。那天我和高兄喝了两瓶啤酒,吟诵了两遍杜甫的诗之后,起身出去了办点事去了。我的记忆力看来还没有减退,颇有当年过目不忘的影子,我一路上还在默念这番杜甫的肺腑之言。“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当我去年回来的时候,何尝不是这种感觉;“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我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虽然现在我们只能喝喝啤酒,但是与知己对酌,不管是什么酒,又有什么关系呢?“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默念到这句的时候,我已经不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三年前的春天,我何曾想过和老朋友一起吃顿韭菜呢?那时我在干什么呢?我在享受人生中美妙的爱情,还是仅仅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狂欢,做一些毫无意义,浪费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三年后的春天我像落魄的杜甫一样和好友一起坐在一起,“一举累十觞”吗?念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时候,我便不能自持,泪如涌泉了,我甚至都无法继续走下去,而是退到一个阴暗的街角,偷偷搽拭自己的眼泪,在后面的路上,我不敢再去回想这首诗了,对现在的我来说,它代表着些许蕴籍,但更代表着沉重的人生。
或许我还不够豁达,东坡先生的心态吾辈难道只能仰视吗? 流过泪之后,才更会像个男子汉,只要不要每天像个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就是了。不管是因为什么,都不要把过去的苦难看作一种负担,即便都是自己的错,那又怎样?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武亦不幸免,吾又何己咎乎?杜甫可曾这样过?还是苏轼这样过?在感悟到了这些,还有前面两位都没有机会遇到的莫扎特之后,我就更没有理由这样了(C)。
2013年4月13-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