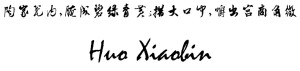我一直都想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写在2013年圣诞节期间的那次中欧之旅(行程可见我的另一片文章《呕心沥血一下午排的旅行计划表》),尽管是一次非常拮据的穷游,但是我的确是去了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去的两个城市:维也纳和布拉格;另一方面,我却不知道该整理这次旅行中的各种情绪和感触,它们到底是兴奋的、激动的、迷茫的,还是忧郁的?虽然我无法确切地说到底是哪一种情绪主导了这次旅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每当我想起在黄昏中穿梭在中欧乡间的Euroline,孤独而又落寞的古城街道,还有在冬天的微风中轻轻抖动着暗白而又有力的肌肤,不停挑逗着无处下脚的河鸥的多瑙河,我脑海中总是回想着在曾经也在这片土地上频繁来往的莫扎特和他的音乐,尤其是A大调交响曲(K201)。
可能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情绪也像K201那样复杂,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事实上,我是很想去萨尔茨堡看看的,K201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时期所创作的所有交响曲中的巅峰之作,甚至在莫扎特的所有交响曲中,它都算是一首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虽然相比在它之前的那些早起交响曲,失去了童年和青年早期莫扎特参杂了他自己和J•C•巴赫、海顿以及其他曼海姆乐派风格的童趣和清澈,而相比它之后的,尤其是维也纳时期所创作的几首后期交响曲,它又没有后者的严肃、沉重和对后世交响曲发展方向的深远启示。但是其他作品也没有这首交响曲所独有的朦胧,无论是谁,都会对莫扎特在这首短小但精细复杂的交响曲中把诸多情感和格调精确而又流畅地编织在一块的鬼斧神工所倾倒,它不像是一首过渡型的作品,更像一个即使对莫扎特这种天才来说都算得上天才之作的灵光一现,它本身便是一个启示,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启示,而不是作曲技术本身的启示。
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也特意去过一趟莫扎特纪念馆,也许是因为它现在已然是一个人声喧哗的旅游景点了吧,可能还不如海顿或者贝多芬纪念馆安静,除此之外倒没有太多地直接和莫扎特的遗迹所接触。这次旅行还有好多地方要去,比如茜茜公主的王宫、美泉宫,还有维也纳市区包括斯蒂芬带教堂在内的诸多名胜古迹,毕竟这次维也纳之旅不是莫扎特之旅。但是,我却仍旧能够深深地感觉到,整个维也纳似乎都涂上了一层莫扎特的色彩,尤其是在晚上,我越发感觉到自己放佛就在放大了的莫扎特的音乐之中行走。由于时间安排很紧张,我和同游的孙兄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段,在12月24-26日的晚上分别去了维也纳大学校园、美景宫和奥地利的国会大厦等景点。在夜晚的维也纳大学里面,我还是生平之中第一次感觉到哲学在大学中的尊贵地位,我们进入了巴洛克式的雍容华贵的大学主楼时,映入眼帘的便是“PHILOSOPHISCHE FACVLTÄT”(德文:哲学系),这几个字也见证了这个孕育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大学1000年来走过来的历程。除了维也纳大学之外,我们晚间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国会大厦之游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和维也纳其他的传统建筑类似,也一样是宏伟高贵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两旁矗立着十尊左右的雕像,这些雕像都拥有令我很惊讶的身份,它们之中除了凯撒之外,无一不是包括色诺芬和李维在内的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曾经执掌奥地利国家牛耳的国王或者王后。经过这两晚的文化之旅,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对文化和历史无比尊重的国度的文化形态,我想,也正是这些如同莫扎特的K201第一乐章一样纷繁复杂但又细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生命线构成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的生命脉搏,从那时候,我对人类的文化自觉重新又燃起了信心,至少奥地利人在尊重哲学、历史和音乐这三个文明的永恒主题。
相比下来,我对比较大众的经典比如美泉宫、斯蒂芬大教堂反倒没有如此强烈的文化冲击感,可能因为它们已经比较商业化了吧。在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反倒不容易感知到它们低下的深层的文化内涵,自己也仅仅像其他的摩肩接踵的游客一下,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见证物浅尝辄止,照几张照片,瞻仰一下那些精美的雕栏画栋,便马不停蹄地出发去布拉格了。
坦率地讲,虽然布拉格和维也纳相比,已经是一个显得很简朴的小城市了,和天主教传统下的富丽堂皇的维也纳不一样,一直都向往新教,想挣脱天主教羁绊的布拉格的建筑也像它的宗教倾向一下,对那些奢华的雕饰反而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和自然更加贴近,更加简洁。但是它的商业化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当我们行走在这个波西米亚世界首都的街道上时,丝毫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厚重和忧郁,无论是在圣维特教堂,查理大桥,还是老城广场,路上都是圣诞节期间来此履行的世界各国的游客,用娴熟的英语兜售小物品的当地小贩,还有被这些如蚂蚁一般密集的人群环绕着的再不宁静的一个个的古老建筑。查理大桥上的那些雕像每天看着下面的世界人来人往,看着桥下面的沃尔塔瓦河奔腾流过,或许早已经在这种当下的喧嚣和长久的苍凉的交感之中习以为常,用它们深邃而又孤独的眼神远眺着大河流向的方向,注视着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沃尔塔瓦和它两旁的森林和原野,送走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尘嚣。
在莫扎特时代,布拉格是最理解和赞赏莫扎特的一个城市。莫扎特在《费加罗的婚礼》、《后宫诱逃》等歌剧上演后,都曾经抱怨维也纳的民众不懂得欣赏他的音乐,但是这部歌剧在布拉格的上演却非常成功,莫扎特成为了被布拉格音乐评论家和市民争相追捧的明星。甚至布拉格市还邀请莫扎特常驻此地,虽然莫扎特最后没有搬到布拉格常住,但是的确常常来这个城市演奏他的最新音乐,还专门为他自己于1787年初第一次布拉格之行,谱写了一首交响曲,即他所做的五首后期交响曲中的第二首“布拉格”(K504),这首交响曲也是莫扎特晚期创作的海顿风格的三首交响曲中的第二首。这种海顿风格,仅仅是形式上的,比如第一乐章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柔板引子,直到现在我也还没大搞清楚为什么海顿写交响曲特别喜欢在第一乐章前面加一大段冗长的柔板引子,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下来,但是莫扎特仅仅坚持了三首,从他革命性的第四十交响曲开始便抛弃了这个海顿引子,当然,此后莫扎特仅仅有时间再写一首革新风格的第四十一交响曲,便撒手人寰了。“布拉格”交响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仅仅三个乐章,省略了小步舞曲乐章。这种三乐章形式的交响曲更接近早起的意大利式交响曲,有的评论家认为莫扎特之所以如此反常地使用这种早期的交响曲形式是为了迎合布拉格的音乐习惯。因为虽然当时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奥地利,德奥式的四乐章交响曲已经是主流,但是仍有一些地方流行三乐章的意大利形式;同时,和莫扎特关系很好的布拉格作曲家Josef Mysliveček的创作基本采用的是这种三乐章的形式。也许是为了弥补第三乐章的缺失,“布拉格”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正常演奏时间长达14分钟左右,因为莫扎特使用了一个他的交响曲中最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柔板引子,或许只有布拉格人才能忍受这么一个长引子吧,但是莫扎特的交响曲肯定没有让布拉格人失望,在这个长引子之后,莫扎特便一下子甩出了多达六个主题的奏鸣曲式的快板。尽管莫扎特习惯于在自己的音乐中倾泻自己的旋律,甚至让听众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但是能够像“布拉格”这样集中了如此丰富的旋律也比较少见。果然,莫扎特的炫技不像他在维也纳收到的“音符过多”这种古怪的评论那样遭白眼,而是获得了布拉格人一致的喝彩和欣赏。
至于为什么是布拉格人而非维也纳人能够欣赏莫扎特,评论界有很多的解释,比较主流的解释大致是因为布拉格当时的经济和人口在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恢复,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因此市民对音乐的需求加大;同时,由于波西米亚人天生有音乐天赋,音乐教育又发达,所以这里的人的音乐欣赏能力比维也纳还高,能够欣赏地聊莫扎特在当时看来非常复杂和新潮的音乐风格。我个人看来,可能还有一种解释。众所周知,以布拉格为中心的波西米亚,一直以来都想摆脱天主教的德国和奥地利而独自发展,因此在宗教改革时期,这里的新教很盛行,为此爆发过两次比较大的战争,虽然后来还是被天主教取得了战争胜利,但是新教的思想仍旧在布拉格人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布拉格和维也纳在文化上根本的区别之一。也因为如此,布拉格人对天主教音乐传统中的重视宗教音乐和意大利风格的歌剧反倒不感兴趣,而是对莫扎特音乐中的重视人的感情和歌唱性的世俗风格显示出了相当的兴趣和接受能力。
总之不管怎么说,在这次成功之后,莫扎特便和布拉格这个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1787年后半年,他又来了布拉格,这次更是带来了《唐•乔万尼》的首演。1789年莫扎特路过过布拉格,但是没有留下音乐。莫扎特最后的布拉格之行是1791年,这次他于这个城市首演了最后一部歌剧《狄托的仁慈》,但是这次的主角不是莫扎特,而是加冕为波西米亚国王的利奥波德二世。同年12月,莫扎特便去世了。对于莫扎特的死,和维也纳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拉格全城的悲痛,布拉格人不仅仅为莫扎特举行了大规模哀悼仪式和纪念演出,还资助了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茨。我想,莫扎特尽管在维也纳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总算高山流水有知音,布拉格人对他的热情和肯定,算的上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值得宽慰的事情,而莫扎特在布拉格留下的痕迹也成为了布拉格这个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很遗憾的是,我这次布拉格之行没有时间去瞻仰莫扎特在布拉格的故居。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的,过度的商业化让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远远低于期待。但是,布拉格之旅也是有不那么商业化的地方的,比如我和孙兄在晚上瞻仰了一下德沃夏克故居。虽然晚上故居已经关门了,但是我们走在寂寥的街道上,才算感受到了这个饱经沧桑的中欧古城的真实的呼吸。布拉格的命运其实就是波西米亚(大致相当于如今的捷克全境)这块土地命运的缩影,历史悠长,文化底蕴独特而又深厚仅仅是它命运的一个侧面,布拉格和波西米亚也见证了血腥的欧洲宗教战争,两次反对天主教统治的“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两次大的战争,主战场都在这里,后来布拉格又成为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和反对苏联统治的前线,也有了以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为代表的捷克民族主义乐派。
在参观了德沃夏克故居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去了高堡(Vyšehrad),去了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长眠着包括德沃夏克在内的诸多波西米亚名人的高堡公墓,它就坐落在沃尔塔瓦河边上的一座小山丘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同时又能俯瞰布拉格城区和贯穿城区的沃尔塔瓦河,这条河从远方的森林和沃野流过来,孕育了布拉格这座特别地让人难以言说的城市,然后重新流向远方的森林和沃野。斯美塔纳便以这个高堡和它下面的沃尔塔瓦河为中心,谱写了浓缩了整个布拉格和波西米亚历史和文化精髓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Ma Vlast)。
可能是我们来地比较早,高堡的人远远没有市中心那么多,反倒多了几分静谧和阴冷。除了公墓,这里还有著名的圣伯多禄与保禄圣殿,再往上走一些,便到了这个山丘的最高处了,往下看就是斯美塔那音乐中的沃尔塔瓦河,而我们所身在的也是他音乐中的高堡。斯美塔那对于布拉格和波西米亚的感情,不像莫扎特那样欢乐而又随心,因为莫扎特毕竟不是波西米亚人,可斯美塔那却是,他对自己饱受战争、天主教统治蹂躏的祖国的感情莫扎特可能理解不了,但是我却有深深的同感,毕竟我对中国也有类似的感触,也只有在这种对祖国的怜爱和悲恸之下,才会有像“沃尔塔瓦”这样流淌着作曲家自己鲜血和生命的音乐。斯美塔那一生的灵魂都集中在了这首交响诗之中,他似乎生来的宿命就是完成这部交响诗,然后便发疯离去了。也只有亲眼见到沃尔塔瓦河我才相信,斯美塔那为什么愿意为这条河流献出自己整个的生命。越过半人高的砖墙和木栅栏,沃尔塔瓦河像一个裸体的圣女一样静静地躺在了波西米亚的土地上,冬日的苍天和空气也都和慵懒的河水一样,相互交融在了一起,只在远处的天边替若隐若现的群山勾勒出了柔和而又简单的轮廓。树叶已经落尽的森林就生长河的两边,在它们的后面是农田和坐落在两岸高丘上的教堂和房屋。在宽阔的大河的映衬下,这些森林和房屋显地很小,放佛变成了女巫手里的道具,一切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条河是真的,只有它是在徐徐流淌着的,但是流淌在这条大河之中的,不仅仅是那对身后的一切都毫无眷恋的河水,还有那些森林和大地永远不会放弃的对生命的追寻,波西米亚历史中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灵魂和故事,和只有在音乐中才能感觉到的自豪、沧桑以及乡愁杂糅在一起的波西米亚的味道。看了高堡,我再不会抱怨这次布拉格之行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满意了。
结束了高堡之行,我们的中欧之行差不多也结束了,虽然后来我们还短暂在布拉迪斯拉发停留了一晚上,但是没有时间去它的市区去看了。我们第二天便坐飞机回到了比利时,尽管比利时有和维也纳、布拉格类似的建筑和人,但是却丝毫没有这两个城市中的那种感觉。或许,这一次中欧之行远远不足以让我真正地领略这片复杂而又安静的土地的一切,但是我并不知道,下一次将是什么时候来这里,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的。
201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