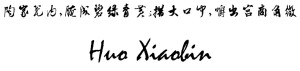昨天,从新闻上得知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于2016年3月13日去世。这则新闻在其他人眼中,可能还不如前几天去世的Alan Rickman的新闻有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普特南的死,触动却很大。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在哲学界混了,但是毕竟是学过六年哲学的正宗的哲学科班毕业生,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科班毕业生中极少的几个当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以极高的分数报了第一志愿哲学专业的人。作为一个曾经立志于献身哲学,后来又被迫逃离出哲学界的人,面对现在世界上少数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而却没有足够的人才接过他们衣钵的现实,我竟然也有一种兔死狐悲,“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冲动。我又想起了前几天和我同为人大本科校友的哲学讲师江绪林自杀的风波。他刚自杀的那几天,似乎在现在这淌思想的死水中引起了一些波澜,但是也就一些波澜而已,没过几天,人们的视野便又转移到了火爆的楼市上去了,而江绪林已经很快就被媒体所遗忘和抛弃,他所带走的,似乎只有他自己一生无尽的惆怅和遗憾一样。或许,再过几天,普特南也会像江绪林一样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他们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寿终正寝,一个是正当壮年却自杀而亡,这或许也昭示了美国和中国的哲学学者所处的不同的境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死亡,却也共同地显示了哲学所处的困境。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应该写写我在人大六年期间读哲学的一些往事,我的学习经历和其他人比起来,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既学过哲学,又学过金融,还将要去学法律,而且都还是在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接受的这些人文和专业的教育。但是哲学教育和后两者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如果说金融和法律是塑造了我的“才”,那么哲学是塑造了我的“人”。我是在V Business School,学会了做PPT,学会了计算股票和债券的价值,学会了写Equity Analysis Report,学会了西装革履地和别人强颜欢笑。
但是,我是在人大哲学院的六年间,深入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和价值观,可以说,是这六年,让我这个人在有“才”之前,先有了“灵魂”。在高中升大学之前,我是准备一进去就入党的,但是在人大哲学的六年中,当我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有无数次的入党机会,甚至学院党委专门找人过来催我,我最终还是选择做一个群众;在这六年中,我从一个对穆斯林和同性恋都没有任何认知的人,变成了一个纯粹和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也是在这六年中,我想明白了我这辈子究竟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意识到我只有从哲学学术界逃离出来,我才有可能完成我人生的使命,这就是《政府论》的写作,这部我把它定位为对中国人进行一次启蒙的著作现在在以平均每天1000字的速度成长着,而为了给创作这部著作的我提供基本的支持,我必须去商学院和法学院学习让我能糊口的“才”,让我能有份工作,让我能够在创作的时候保持完全自由的思想。
虽然总的来说,我对在人大哲学院六年的生活的评价是贬多于褒的,但是我依旧很庆幸在这里遇见过很多我今后不大可能遇到的真正的学者,读过很多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书,思考过很多现在的我都觉得好笑的大问题,甚至我到现在为止唯一花痴过的美女,都是在人大遇到的。在从人大毕业后的几年中,我遇到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尤其是女人,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灵魂,所以,在我和她们的视野中,世界是不一样的。对她们来说,户口,金钱和房子是生命的全部,而对我来说,这些什么都不是,也是因为如此强烈的现实冲击,我才一直都有反思一下我学习哲学的经历的想法,今天遇到了这个契机,便开始下笔了。
佛教把释迦摩尼圆寂之后的时代分为三个时期:正法时期、像法时期、末法时期,我也斗胆依葫芦画瓢,把哲学也大致分为三个类似的时期:老庄和柏拉图的时代算是正法时期,从康德到尼采算是像法时期,而二战之后算是末法时期,而以罗尔斯,普特南为代表的这一批哲学家正是末法时期的哲学最后的几个代表。其实,作为一个真正喜欢哲学,即使离开了哲学学术界,但是仍旧没有放下哲学的人来说,这么定位现代哲学,我也是很悲伤的,然而在我看来的确如此。哲学最高峰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而自尼采之后的世界发展大势也决定了哲学必定会走向衰落。
一方面,哲学曾经是科学和艺术之母,在十九世纪随着学科的分化和成熟,以前曾经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都变成了独立的学科,现在我们所说的数学,物理等学科都曾经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已,随着哲学分支的不断独立,哲学的内核也被一步步地空心化,最后留下了一些边角料成为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说,二十世纪哲学走向分析主义和语义哲学的方向,是有其本身的无奈的,不是哲学家们乐意钻这个牛角尖,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除此之外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突破的方向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满清时期的汉人文人一样,因为一些主要的问题不能研究,所以只能到故纸堆中研究训诂和文字,虽然也都做出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是终究是空洞无物之学。
另一方面,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和社会分工的极度细化,商业和法律开始了大规模地发展,并且渗透进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整个人类社会开始走向全面的职业化和世俗化,不再像古典社会那样慢节奏地发展,会有很多精英选择哲学,艺术这些纯粹精神领域的职业,所以现代社会的精英开始流向了法律、医学、商业和技术等领域,而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等无法创造世俗价值的学科就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自然越来越衰微。
因为这两个原因,哲学在现代已经从以前的科学之父变成了如今的一个边缘学科,再加上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很容易就出现某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大师去世的时候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的状况。
同时,因为中国落后的教育体制,哲学研究的困境越加严峻。因为中国现代的教育体制总体来说还是沿袭了苏联的计划体制,所以在大学招生的时候,各个专业都会按照一定的计划招到一定的名额,对于那些热门专业来说,这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几乎没有人愿意学的冷门专业,比如哲学,如果报志愿的人少于计划人数,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学招生现象:调剂,进而导致一大批根本对哲学没有任何兴趣的人进入了哲学学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负责这些人的毕业后的去向的,后来随着高校就业的市场化,国家已经不负责就业,按理说,计划经济的产物调剂应该也随之终结,但是并没有,这就导致许多根本对哲学没有兴趣的人进入了哲学专业学习,而在就业的时候又就不了业,出现了目前哲学专业非常可悲的境地。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现象:学哲学的人反而是对哲学最没有兴趣的人。这些人对哲学的消极态度,进一步导致哲学研究后继无人,即便其中有少数几个人是抱着献身哲学的感情来的(比如曾今的我),但是在这种非常可悲的氛围之下,那几个少数真正热爱哲学的人也会对哲学学界产生失望,进而离开。我2003年考入人大哲学系时,全班38个人只有两个人是第一志愿报哲学的,最后这两个人都离开了哲学界了。
可以说,哲学的衰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而真正可悲的是,我作为一个个体,却无能为力,如果我坚持下来,最终的命运估计比江绪林好不了多少,毕竟这是一个时代潮流,我一个人是阻挡不了的。想到这一点,我也是唏嘘不已的,因为我亲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学科一步步沉沦,也因为如此,我就把我在人大学习哲学六年之间所经历的人,所经历的事回忆一下,记录下来,聊作对自己的曾经一段学术梦想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