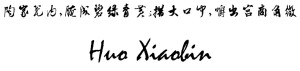新年新气象,自从每天开始早起跑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都好多了。过去半年,受周围不良的熬夜风气的影响,觉得每天不干到凌晨两三点,就会落后别人,结果老是熬夜,但是自己的生物钟又不可能马上就变,还是每天六点就醒了,弄地自己睡眠不足,白天没有精神,连连打呵欠,还得强忍着不能睡觉,晚上也没有精神,还得强忍着熬夜,导致恶性循环,最后下来,效果很不好。这几天放假,我终于有机会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决定以后不能再熬夜了,这都是现代社会一个非常不好的价值观。哲学中有一个说法叫“集体无意识”,就是整个社会群体追随一种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关心和质疑过,只是每个人看别人这么做,就下意识地想“大家都这么做,准是没错的,自己也要这么做”。现在的社会也是,到处都充斥着熬夜文化,还有什么“睡你妈,起来嗨”之类的网络语言,结果很多人以为这种熬夜文化代表着一种年青活力,代表着一种酷炫,这真是一种肮脏的价值观。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沦落到“集体无意识”的旋涡中,随波浊流,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受害者呢,要不就白读这么多书了。那些现在还年轻,熬的了夜的人,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十年后就会后悔不已。
我现在每天,都是晚上十点睡,五点准时醒,刷牙洗脸,敷个面膜,然后就到中山公园去跑步,沿着跑道跑三四个来回,差不多五六公里,跑完之后大汗淋漓,感觉每一个细胞都从沉睡中被唤醒了,然后白天感觉神清气爽,才发现自己已经两年没有锻炼了。我其实一直都有早期跑步的习惯,但是在北京的那几年,因为雾霾太大,不敢跑了,一下子就荒废了两年,也是在这两年,我的身体状况特别差,三天两头跑医院,但是除了咽炎,医院也查不出其他病了,我觉得我就是处于亚健康状态,身体处于似病非病之间,这就是免疫系统提醒要我锻炼身体的信号。现在很多人都买什么健身卡,去健身房,我以前好多同事都这样,其实根本去不了几次,浪费那么多钱无非就是随随大流,装装B而已,其实最便宜,也最有效果的健身方式就是坚持跑步了。我的三姨夫都九十多岁的人,至今无病无恙,能跑能跳,还得照顾我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的三姨,我有一次问题他怎么能身体这么好呢?三姨夫说就是年轻时在四川当兵的时候每天部队都会拉出去跑十公里打下的底子,后来转业回了山西,他其实就没有再锻炼过了,但是就靠在四川二十多年拉练的底子,老人家活了九十多都比五六十的人精神和健康,所以,年轻时的锻炼真的是很重要的,老了才知道年轻时打个好身体底子多重要。
再加上现在结婚这么难,我要做好一个人活到老的心理准备,所以年轻时候要是不把身体锻炼好,老了病怏怏的,连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那就太凄惨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17年十月我去Magistrate Court的时候,听的是一个普通袭击的案件,被袭击者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结果作证的时候,根本不记得他被袭击过,法官一问三不知,最后无奈不让他作证了。同行的其他人都笑这个老头太搞笑了,连自己被打过都不知道,唯独我觉得很悲哀,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担心自己老了也成这样。可能同行的人还是没有体会到死亡和衰老对一个人的折磨。我这几年却频繁和死亡近距离接触,所以感触也不一样。其中最触动我的就是16年时一个同事的猝死。前一天的时候我还和那个人争论这个客户该怎么处理,互相打听你今年的奖金多少钱,什么时候涨工资,还不忘说说黄段子,第二天那个人便躺在医院的停尸房了。当时我在一天的时间里整个人生观都似乎奔溃了,在死亡面前,什么客户,什么工作,什么工资,屁都不是。
后来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还写了半篇《论死亡与永恒》,才算把自己碎成一地的人生观重新拼合起来。过去的半年,我又陷入了对工作,收入和婚姻等人生琐事的纠结状态,搞地自己很紧张,但是现在想想,这些东西和健康以及生命比起来,真是连个吊毛都不算。法律界这么高的门槛,并不是这个行业有多高尚,只是因为最开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设置了这么高的门槛而已,一方面这些已经入行的人需要有新人给他们打工,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过多的新人分他们的蛋糕,所以才导致入门竞争这么激烈,无数的法学院学生为了得到这行的入场券,不惜勾心斗角,拼地你死我活,不惜牺牲健康熬夜看书,就算拿到intern,签了TC,进入之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在高级办公楼工作的律师,别看男的西装革履,女的高冷傲娇,但是他们不见得比农村的抠脚大汉,洗头小妹干净多少,背地里免不了充斥着男盗女娼,蝇营狗苟,张爱玲的那句话“华丽的袍子下面,都是虱子”,在现代的社会里,更加适用。所有人拼地你死我活,想要得到的只不过是那件华丽的袍子,而虱子他们是没有兴趣掐死的,反而得到袍子之后,会越养越多,其实抢到袍子的目的,就是养更多的虱子,在一个笑贫不笑娼,没有正直的价值观的社会里,人越往高处走,就越会是这样。
这些都是我今天早上跑步时想到的,想通了这些,就确信什么都不如身体健康重要,所以我以后计划雷打不动地每天坚持这个作息,再也不会随大流,把自己搞成亚健康的中年油腻男。没想到又扯了这么多,现在言归正传,继续扯韩德尔和布鲁克纳。
在前文提到的那个背景之下,今天就特别谈一下韩德尔和布鲁克纳。简单而言,韩德尔的音乐表现的是崇高,是最高境界的人性;而布鲁克纳的音乐表现的是神圣,是最低限度的神性。但是两者的音乐都是只有在德国哲学这篇土壤之中才能孕育出来的。
韩德尔其实是拉莫的同时代人,他们的经历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一开始都学的法律,但是却都出于对音乐的热爱最终还是吃了音乐这碗饭,都是顶尖的歌剧作曲家,又比如他们都服务于宫廷王室。但是,二者更多的是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就是音乐风格上的迥异。韩德尔创作了很多宗教音乐,但是他的音乐自始至终都在表现世俗的人性,这和拉莫的追求是完全相反的,拉莫的音乐里,我们其实看不到人性,只能看到自然,而在韩德尔的音乐里,即便是纯粹的宗教音乐Dixit Dominus(《主上如事说》),我所听到的也都是蓬勃的生命力和对世俗快乐的歌颂。更别说他其他的《皇家焰火》《水上音乐》,即便是《弥赛亚》也到处弥漫这人间的气息。
但是韩德尔的人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是不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其实是宣扬人的动物性,即纵欲和狂欢,而韩德尔的人性是崇高的人性,是向往神性的人性。有可能,韩德尔一直都想用他的音乐来歌颂神,但是他这个人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在现实中韩德尔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Boy,除了是个吃货和大胖子,脾气还非常暴躁,布莱希特的《音乐逸事》里记录和不少关于韩德尔的段子,其中一个我特别喜欢,现抄录如下:
一天楚左尼(Cuzzoni)拒绝唱《奥托内》(Ottone)中的“Falsa imagine”,亨德尔说:“噢!亲爱的夫人,我知道你是个道地的女魔头,但是我会让你知道我是魔王。”说完他将她拦腰抱起,而且发誓如果她继续找麻烦的话,就把她从窗户里扔出去。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德国某些地区以前处决犯人的方式。
可以说,韩德尔的音乐骨子里有他性格中的无限放大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韩德尔的服务对象一直都是贵族和王室,一开始是汉诺威选帝国候,后来又是英国国王,所以他的音乐必须庄重和严肃,久而久之,这种庄严和自我意识慢慢结合成了韩德尔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他在英国的时候写了很多歌剧,这些歌剧不是给王室写的,而是纯粹为了卖票吸引市民来听的商业创作,但是对于给追求单纯的粗俗感官刺激的下里巴人写音乐,显然韩德尔是无法得心应手的,所以他的歌剧最终还是败给了《乞丐歌剧》这种连古典音乐都不算的市井歌剧,最后他不得不转写清唱剧挽回颓势,而清唱剧正好是适合他风格的一种体裁,因为他能够充分地发扬自己最擅长的崇高感。
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韩德尔的崇高的基础是人性,是人性对神性的追求而形成的一种崇高感,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渴望。但是,它不是神,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有神性的音乐呢?这就得去听布鲁克纳了。
布鲁克纳的音乐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听的下去。他的音乐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冗长,沉闷。他的八部交响曲每一部都像一首放大版的弦乐四重奏一样,每个乐章之间的速度,节奏和音色对比都不明显,和声无限地蔓延,一开始听放佛就像一个寂寞的老人不停地喃喃自语。而且他的交响曲的演奏长度也是长出了天际,比如《第八交响曲》,性子急的指挥家也得一个多小时,而如果是切利比达凯,朱利尼这种本身就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指挥的版本,则将近两个小时。
所以说,老拿布鲁克纳装B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听的下去的人不多,即便是我,到现在也就才攻下了第四,第七和第八三首。但是如果破除了前面说的那些障碍,我的确在布鲁克纳那里发现了一个辽阔和神圣的世界,或者说,那就是神性的世界,那个韩德尔终其一生都无法到达的世界。布鲁克纳也把德国音乐从一个简单的素材发展出复杂的音乐体系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通过每一个变位,转调,织体来勾画神性的每一个侧面,当听完一整首交响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刚刚和神完成了一次亲密的邂逅。
从他的那个时代起,很多人就把布鲁克纳粗暴地划分到瓦格纳,马勒阵营之中,仅仅因为布鲁克纳崇拜瓦格纳。事实上,布鲁克纳并不属于瓦格纳一派。瓦格纳的音乐是神秘主义,马勒的音乐我试图听过,但是都因为找不到感觉而放弃了。这里只说瓦格纳,他的音乐虽然是神秘主义,但却是通过人性的扭曲而实现的神秘主义,和神性没有关系,其实是另一种人性,韩德尔是将人性崇高化,而瓦格纳则是表现人性的恶和欲望,并将其理想化。
布鲁克纳的风格其实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欧洲早期宗教经文歌,而他做过很长时间的教堂管风琴师,早期曾经写过七首短小但是代表他成熟风格的经文歌(motet),这几首经文歌的风格预示了后来他的交响曲的风格。如果说传承,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更像是传承了舒伯特的传统,即歌唱性。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其实在风格上是和布鲁克纳交响曲有很多神似的地方,但是舒伯特的歌唱性是一种诗意的歌唱,而布鲁克纳的音乐则是对神虔诚的吟唱,他企图通过音乐来直抵神性,而且他也做到了。他的交响曲中也不是没有世俗的背景,比如他曾经说他的第八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写的是“三皇之战”(即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单挑沙俄和奥匈联军并大胜的经典战役),但是听完之后,我觉得要感受人间的战争,更应该去听贝多芬的“威灵顿的胜利”,而布鲁克纳的音乐则没有丝毫人间纷争的混乱,有的却是庄严的阵列和云霄一般的高冷。
但是我觉得布鲁克纳的性格却是成就他的音乐中的人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提到了韩德尔是个耿直Boy,布鲁克纳则正好相反,他应该是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也可能因为卷入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两派的纷争,备受攻击,形成了谦逊到卑微的性格。前面提到的韩德尔冲女演员发火的场景对布鲁克纳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所做的往往是相反的事情。比如,他的交响曲送到指挥那里,如果指挥觉得看不懂或者不满意,他往往会允许指挥随意进行修改,或者按照指挥的意思自己修改,直到指挥和乐队满意为止。这也造成了他的交响曲版本众多的问题。这种在现实世界中的无限的卑微也映射到了他的交响曲之中,但是这种卑微在他的音乐里面变成了面对神的卑微,反倒成功地将神引入了交响曲之中,或者神只有在布鲁克纳式的卑微和虔诚下,才会降临到人间。在韩德尔那里,尽管他再渴望神,但是他自己的人性太过强烈,神性便与他无缘,而布鲁克纳将自己的人性无限地隐藏,于是神性便出现了。似乎,音乐发展到布鲁克纳的时代,放佛回到了哲学领域的经院哲学时代,布鲁克纳做的是和阿奎那类似的事情,阿奎那用逻辑证明神的存在,而布鲁克纳则用音乐证明神的存在。
而欧洲的音乐,从一开始的帕勒斯特里那时代的纯粹宗教经文歌,到后来反对神的模仿自然,再到韩德尔对人性的崇高化,最后到了布鲁克纳又回到了神,似乎也走完了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历程。布鲁克纳之后,欧洲的古典音乐传统便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