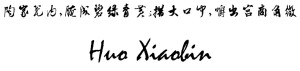佛教不是哲学,但是它们并不是没有关系,而且佛教并不像意识形态教育中所宣传的那样是麻痹人的心灵的工具。佛教和任何的一个思想体系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深刻历史积淀和文化内蕴,一部佛教史,其实也就是一条宽广的由无数人的思想汇聚而成并对人类现状及未来的深刻思索的悠长的画卷。而且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历史出现过很多的哲学流派,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犬儒学派,爱里亚学派,陆王心学等林林总总的哲学流派,但是在哲学史上真正大放异彩的却是每一个伟大哲学家的独特思维方式及他思考的内容。康德个人的哲学体系对与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而言,其意义远远大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在哲学史中,个人的思想是永远占主导的地位的因素,往往是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并决定了一个学派的思想,而不是学派的思想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而且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治很多人并且延续数千年都没有能够被阻断的思想体系。我们所熟知的伯拉图学院延续了五百多年,最终还是在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压制下中断,而这已经是哲学中的极至了。但是有很多宗教却能够成功地延续数千年并且使很多人信服并且虔诚地皈依之。历史上的哲学从来都是哲学家个人的沉思和忏悔,他们很少想要把自己的思想说给大众说,哲学家总是固守着自己孤独的营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正如Hendrik Willem Van Loon所说的:“He has a small income of his own . He had no desire to marry .His wishes were few. He anticipated a quite and happy life and he had it”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加于大众身上,思考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宗教却不一样了,宗教在它创立的时候就有着哲学所不能有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在思考的问题上,宗教有着和哲学一样的思考内容,就是对人生的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事实上远非如此,为什么哲学和宗教所思考一样的问题但是却行走着两条道路截然不同的道路,其实在最终的人生归宿上,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即二者都在思考人生的真正的终级目标是什么,甚或人的灵魂的归宿到底存在与否及它到底是什么,但是为什么是大众更倾向与宗教而不是哲学呢?在对人生的最终的归宿之上,佛教和哲学其实是貌合神离,佛教有着独特的结实方法。
人的归宿一直历史上讨论最为深刻的话题之一。
我不知道对于人类来说归宿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终结?还是一个开始?它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归宿就是当个体的存在已经不能再保证它本身的实在时为个体寻找其脱离原先实在后的存在方式。对人类来说,实在意味着一切,他关心存在吗?当人的实在快要终结时,他难道不应该思考自己存在的去向,甚至当他还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时时候,这个问题对他已经十分迫切,十分有趣了。
对于存在来说,我们不能不说它就是永恒的属性之一。它没有始终,向一条长长的直线一样永远找不到它的永恒性,或者即或能的话,只能依靠我们的悟性来隐隐约约地与存在并肩,倾听存在对它的本质的诉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特性作为理解一切的前提,因此它就是先验的,因为经验之物都是实在者;存在先于现象的实在,实在只能是存在特殊的映象。佛教对人的现实的实在也是有着一定的关注的,实在对于好奇于永恒的存在的人而言,是一个很不幸地限制,因为人只有几十载的生命去理解永恒。实在的短暂性乃我们不得不考虑它的归宿的原因,实在乃存在属性的外化,但我们可以否定实在,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被否定的,但绝不能否定它的本身属性的一般性与脱离实在而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确切的说,寻找实在的归宿就是寻找它的本身属性的归宿,就像我们不需要考虑石头的归宿一样。宗教中对超越的对象的追求正式这个原因,佛教虽然没有像其它宗教一样去设置一个最高的神作为存在的化身,但是它却指引信徒通过自己的修行而不是通过神的指引到达存在境界,超越自我表现的局限。
人的属性是什么呢?是灵魂的实在还是实在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要对灵魂敬而远之呢?人类常常背离自己的秉性而寻找自己根本不关心的东西。这一切最终必须面对一个前提:那就是灵魂的去向。我们不必考虑它的来由,因为它已经存在;但它的未来却并不明晰,需要我们的预言。灵魂之为灵魂就在于它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并思考自己的存在,如果我意识到我的存在,那说明我是有灵魂的。灵魂作为存在的固有属性,当它的实在已成虚无,而作为存在的不可虚无性又迫使它在实在之终结后自身却不可能走向终结,它会有另外的世界,这就是它的归宿。
如果有的话,那人的归宿又是什么呢?
在基督徒的眼中,人死后灵魂将会去三个地方中的任意一个:地狱——炼狱——天堂。我们从但丁的长诗中能清晰真切地感受到这三个世界;;黑格尔是信仰他独具特色的三段论的,最后得出结论:世界精神是一切的终点;尼采则颇具东方气息,他创立了“永恒轮回”说,人所摆脱不了的轮回就是他的归宿;曹雪芹说:“树倒猢狲散,落的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只为他人作嫁衣裳。”人的悲哀就在于他不肯去故乡,而只是在他乡嘶哄,以至“自问孤鸿何处去,不知身世自悠悠。” 而在佛教徒的眼中,人的最理想的归宿就是涅磐,那时人超越了痛苦的轮回,成为了真正的“自在之物”,正如唐代诗人王摩诘说的:“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但是无论尼采,还是曹雪芹,无疑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无论如何,每个人对归宿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人死以后的事,它与死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只是寻找可以把自己灵魂的一切深情,痛苦,狂喜与失望寄托到它那儿的一个处所。如果这样,尽管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但它这时都成了我们的信仰。
对人的归宿的确定无疑的把握就是人的信仰。
人可以分为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前者只关心人的实在,而后者则关心人的存在。前者生存的唯一目的是得到满足,而满足的标准不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生活的特别努力,却很痛苦;后者目标仅仅是得到幸福,在他看来幸福的标准是唯一的,因此他的生活确定而从容。
当人的内心从来没有考虑反省,对民族的反省,对人类的反省,他就根本不会有信仰。他的灵魂像是被抛弃的天鹅,飘无定所,而他本身也不过在一生中作毫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信仰可以使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起来,可以使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它是人对自我的爱,这深沉的爱决不止一生的享受,决不止短暂的荣华;信仰所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当它把人的命运把握时,生命对我们来说就不再复杂了。是的,它原本就不是复杂的。叔本华鼓励人去死,那是错的。他仅仅把归宿看成是死后的事,但在人的生命中他还有东西必须找到寄托。爱情,理想与自我实现的被承认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在信仰的支持下,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否则我们的结果是不完美的。
一个超越的人的实现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取决于人对哲学的兴趣。但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有信仰的人当他真诚的对待自己的信仰时,他离自己的归宿已经不远了,换一种说法,就是完美的人。信仰对于有信仰的人而言是生命的终结,但信仰的终结最终成为了永恒。只有它能够回答,人的真正归宿是什么。那不是一座冰冷的坟墓,那是永远的宁静,那是谦卑和自省所营造的人的灵魂最虔诚的殿堂。我们的内心在那里,他仍然跳动着,我们的思想在那里,他仍然思考着。存在延续着他自己,就在这里,因为它是永恒的。
有信仰的人中,或者对此确信无疑,或者仅仅是不屑一顾。他们必须面对如何协调自己现实的实在与非现实的后实在状态的冲突,为此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禁欲与纵欲。前者是对后实在的信仰有极高的责任,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不致使自己多年之后内疚不已,一个人只能做他良知允许他做的人,而他必须控制自己良知的宽容界限使它能够对自己的信仰毫无亵渎与污辱,这种人被世人称为信道者,但无论如何他们做到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支配难道需要担心他人的议论吗?无论何时,无论你如何盲目地嘲讽他们,过度的纵欲都是对自我的背叛。纵欲者认为不需要对后实在的信仰承担任何责任,而现实的实在又是短暂的,那他必须在它还未消失前尽情消受它,或者蹂躏它。于是在这时有信仰的人甚至比没有信仰的人可怕,如果后者是吝啬人的话,那前者就是醉鬼;后者认为现实的自我就是一切,因此竭力想保护它;前者真好相反,认为现实是虚无缥缈的,根本没有必要保护它。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这是信仰的两个极端,它在一些人身上显现必然会使他们分化,这正是人的归宿最令人费解的问题。
那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它?如果相信它的话,如何避免信仰悲剧的发生?如果不发生的话,你能找到人生更好的归宿吗?我们应不应该时刻反省内心,我们到底能不能超越实在的自我,难道有可能就因为一个棘手的节点而造成整个信仰体系的崩溃,使人的最终走向重新暗淡无光,使人类仍然在黑暗中毫无意义地度过一生,而他最终会停留在哪我们却一无所知吗?是恐惧还是向往,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对生的毁灭的恐惧还是死的来临的向往?那支配一切的存在为什么不在人类困惑的时候向他提供一点足以使他片刻安息的线索呢?难道人类在毫无意义地走完自己的行程时当他还无法将自己的感受,自己灵魂所看到的一切传递给依然对自己的归宿没有明确看法的后来者时忽然坠入自己一无所知的深渊吗?无论这深渊是天堂还是地狱。
前面我们谈了大量关于归宿的事情,那么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人的归宿呢?
佛教是富与理想主义和超越精神的宗教,实现超越生死的痛苦,获得人生的解脱,成为自由自在的境界,是佛教修行的目的所在。佛教中对人的最终归宿有着丰富的概念,比如涅磐,佛,如来。自性,实相等,其中涅磐是最重要的一种解脱方式。涅磐又译灭,灭度,寂灭,圆寂,是指消灭了烦恼,痛苦及产生原因的境地。
部派佛教通常视涅磐为一种灭除痛苦的状态和境界。如《杂阿含经》卷18云“涅磐者,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磐。”那时还把涅磐分为有余涅磐和无余涅磐,而后者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人生的最高的归宿,《中阿含经》卷四十云;“涅磐者。无所依住,但涅磐灭讫,涅磐为最。”有余涅磐虽然断除了烦恼,但是仍有肉体残存,肉体是残余的身。有余涅磐既已灭除了烦恼,又灭除了以后生死流转的因,但是作为过去世造成的果报即肉身仍然残存着,活在时间,而且还有思维的活动,因而这种涅磐是不彻底的。而在无余涅磐之境界当中,不仅灭除了烦恼,生死的因,也灭除了烦恼,生死的果,灰身灭智,死后不独肉体不复存在,连思维也不存在了,生死的因果一起灭尽,一切归于寂灭状态,获得彻底的解脱,这时候最高的理想境界。一般人为,释伽牟尼在普提树下悟道成佛只是达到了有余涅磐境界,直到八十来岁逝世时,才是真正进入了无余涅磐境界。
可见佛教中的人的归宿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一个境界,虽然它是和人间的生老病死,欲望瓜葛没有关系,但是却是与之相对立的,往往不像哲学那样从一开始就在超越经验的角度上思考。而佛教的涅磐其实并不太喜欢思考,它认为人要得到解脱,就必须脱离人所固有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思考,一旦人能够连思考都能断弃,那么他就可以获得真正的涅磐。在这一个方面上,佛教是隐性地人的现实欲望相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只要能够断弃现实的欲望就可以达到涅磐的境界的,这种涅磐不是通过思考来获得的,而是通过修行,也许这种修行本来是非常反感于思考的,因此在本质上,佛教中的涅磐和哲学中自由还是有所区别的,而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
对人的最终归宿的不同理解,佛教只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来解释人身后的去向,是和它作为一个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宗教一开始就不是个人的活动,正如释加牟尼在创立了佛教后就招收了很多的门徒一样,为什么佛教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和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息息相关:普度众生。佛教徒眼中,不仅仅他们自己是应该得到超越,而且还有其他的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一样要得当解脱的。解脱无论对于哪一个人,都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问题在于你修行的火候到了那种程度。
那么在佛教徒眼中,人的归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谁也不能够确切地描述这一点,因为它如同哲学中的自在的世界一样是不能够在经验的角度来理解和考察的,他们所能告诉世人的就是:它属于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再也没有人世间无休止的罪恶,没有人在压迫别人,也没有人再为反抗压迫而做出生命的牺牲,所有世间的不合理和罪恶在人达到了这个归宿之后就都不见了,人摆脱了世间一切贪瞋痴的束缚,不再为一点的小事而花费自己无尽的心血。也许这正是佛教吸引人的地方,它只需要人去放弃,因为在世间一切人所做人所想,都是徒劳无益的,都是与己无益的,什么要让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变成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每日为了这些事情而操劳憔悴呢?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看到了自己当前状况的不足因此想获得更多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这真的是自己所需要的吗,难道追求那些身外之物都是自己一生奋斗的价值所在吗。有言“金钱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人临近生命的终点时,他才会明白他所需要的——无论他以前相不相信——是灵魂的超脱和永生,无论哪一个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身后达到一个无欲无求,自在自然的世界的,而这正是佛教能给予我们的,也许在这一点上佛教给予了世人这种超越心理一种现实的依靠,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试想当年佛祖率领早期的诸位信徒苦修以得正果,然后有传经天下,普度众生,或许我们从中就能够找到佛教的真缔所在。
(本文是大学时期《佛教史》课写的一篇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