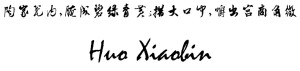作为一个忠厚老实的山西人,我也算是一个性情中人了,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喜怒能形于色,而且现在我对生活的满足点已经低到不要再有想想就反胃的小组作业就行了,上周给国内的高兄通话的时候,他竟然听出我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这还真是事实,一想到再挺一周,就可以和小组作业说再见了,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难免就表现出来了。至于前几个月怎么度过的,我都不想再去想了,有时候连自己最喜欢的莫扎特都没有心情去听了,但是在这几个月中,却有一首非常冷门的序曲成了我的最爱,也是它陪我度过这有生以来非常难熬的几个月,它就是贝多芬的《斯蒂芬王序曲》。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整套的200套(400张)的DUO系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古典录音系列,基本涵盖了古典音乐所有重要和不重要的曲目,而且多出自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名家演奏,其中的一套《贝多芬序曲全集》收录了贝多芬的所有序曲,不仅有比较流行的《艾格蒙特序曲》《克里奥兰序曲》,还有一些很少被演奏和录音,但是其实非常优秀的序曲,当然,其中便有我如今的最爱:《斯蒂芬王序曲》。这首序曲的编号是OP 117,已经属于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了,但是风格却和同样属于晚期作品的《莱奥诺拉序曲》大相径庭,或者可以说,这首序曲的风格和贝多芬的大多数晚期作品都非常迥异,首先是贝多芬应用了匈牙利舞曲的节奏,但是他对匈牙利节奏的处理又和后来写过著名的《匈牙利舞曲》的勃拉姆斯不同,后者注重挖掘匈牙利舞曲中的忧郁感和民族风格,但是贝多芬却力图还原它作为“舞曲”的性格特征:欢乐,无拘无束,即便序曲的主题是非常庄严的斯蒂芬王的事迹;再者,尽管序曲的主题和《艾格蒙特》《克里奥兰》等非常类似,都涉及了英雄主义和历史背景,但是贝多芬在这首序曲中却一反常态,对他一贯热衷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灵魂深处的升华不屑一顾,而单纯地展现了一种十七世纪风格的欢愉和悸动,这种纯粹的音乐精神甚至在贝多芬的早起创作中都不多见。
但是转念一想,这首序曲的情感抒发如此独特,可能和它的主题有关,这首序曲其实和《艾格蒙特序曲》一样,是为一部话剧所做的一系列配乐中的序曲。顾名思义,这部话剧是当时一个德国剧作家根据匈牙利第一位国王圣斯蒂芬的事迹写成的,贝多芬为这部话剧写了序曲和九段配乐。这位仁兄乃匈牙利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他的匈牙利名字本叫伊斯特万,后来带领匈牙利人皈依了基督教,结束了匈牙利人在欧洲作为一群异教徒的历史,应该说这在匈牙利历史上算得上是开天辟地的事了,所以联想到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对贝多芬的这部序曲之中无处不留露出来的单纯地像是开辟鸿蒙般的欢乐和一种返璞归真的自信不会产生什么意外了,看来,贝多芬的这首序曲写地还是挺应景的。
说到这位伊斯特万,他活跃的年代正好是中国北宋初期,那个时候,华夏文明已经日臻成熟,发展到了顶峰,可当初被我的本家霍去病赶到欧洲的匈奴人的后代马扎尔人还处于半开化的部族时代,他的父辈都是匈牙利的部族首领,当传到他的时候,带领匈牙利人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统一了匈牙利各个部落,奠定了现代匈牙利国家的版图,因为他的一系列“文治武功”,死后便被封为圣人,得名圣斯蒂芬,在匈牙利的地位相当于炎黄二帝在中国的地位一样。
匈牙利人不仅仅把他封为圣人,在他死后还做了一件听上去有点“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他去世若干年后,匈牙利人又打开了他的坟墓,发现了右手还没有腐败,便把它保存下来,以供他们永世膜拜。匈牙利人的恋尸癖在此暴露无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恋尸癖其实是西方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相反,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是绝对没有这种怪异的癖好的。尽管古代的中国帝王会为自己建造非常豪华的坟墓,但是他们所求的不过是死后能够“入土为安”,却不希望死后自己的身体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暴漏在众人的面前,不管他们是为了羞辱还是膜拜。
中国其实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视祖先崇拜的国家了,但是祖先崇拜已经进化成对祖先之法的崇拜,而不是对祖先身体的崇拜,我想这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世俗气息是分不开的。自古至今,宗教精神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最多只是一些士大夫在失意的时候聊以自慰的精神寄托而已,而恋尸癖恰恰是宗教的一个衍生物,中国古代所能找到的不多的和恋尸癖能关联起来的怕就是佛教的“舍利子”了吧,舍利子就是一些得道高僧圆寂火化之后产生的某种不知道是什么的东东,弟子们把舍利子拿回去放到塔里保存,这也是塔的来源,这应该说是一种恋尸癖的变种,不像西方宗教那么明显,毕竟佛教算是所有宗教中最世俗化的一种了。中国人有种错觉,就是佛教是不允许吃肉娶妻的,其实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佛教是允许喝酒吃肉玩女人的,每个80后的人都知道的聪明的一休其实在成年的时候就是一个色狼,晚年还包养着一个盲女供他赏玩,他还引以为傲,写了好多狗屁不通的诗把这些淫秽往事记录下来,连宋朝“奉旨填词”,一辈子住在风月场所,死后还是靠一群有情有义的妓女出资埋葬的柳三变都要自愧不如了。中国的佛教徒不能吃肉,不能娶老婆其实都该怪南梁武帝萧衍,你说他一个九五之尊,在位48年,把“华夏尚未统一,同志还需努力”忘得一干二净,一天到晚玩先把自己关在庙里,然后让大臣再把他高价赎出来的行为艺术,还规定佛教徒不准吃肉和娶老婆,最后还是遭了报应,不仅害地自己饿死,更害惨了日后的一干和尚,只能偷偷摸摸地偷腥,哪像人家日本韩国的和尚爽歪歪的。
闲话先不说,西方文明倒是一直都有一种恋尸癖的传统,君不见埃及的“木乃伊”,耶稣的裹尸布,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对尸体的迷恋吗?这和西方浓厚的宗教情节是分不开的,很多宗教的早期其实就是一种哲学信仰,信徒思维水平比较高,所以可以接受完全理念的信仰,但是随着宗教的传播,主要的信徒从一开始的学者转变为普通的民众,这些芸芸众生当然没有纯理念的思辨精神和兴趣,他们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供他们膜拜,于是便产生了偶像崇拜。基督教传说的耶稣被钉死之后三日在自己门徒的守候下尸体重新“复活”其实便是对基督教早期信徒恋尸癖的委婉的描述而已,只是因为这些下层百姓没有埃及法老那么高超的反腐技术,无法保存耶稣的尸体,于是便说耶稣其实复活并且得到了永生,并且把耶稣画像想象为耶稣尸体,以资膜拜。这种愚昧的做法曾经遭到过另外一些基督徒的反对,尤其在东罗马非常明显,甚至后来演变成持续100年之久的“毁坏圣像运动”,但是最后圣像派依旧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到了近代,恋尸癖在社会主义国家终于被发言光大,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近代化的宗教而已,因为它符合了宗教几乎所有的特征:对乌托邦的信仰,对个人领袖的盲目崇拜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和排外,当然,还有它们的“恋尸癖”,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他们第一代领袖死后的尸体保存下来,放到水晶棺里,苏联甚至做了两个这种干尸:列宁和斯大林,而现在的中国北京某处,不也陈列着一具这样的干尸吗?
从这总意义上来说,中国至少在现在,至少在思维上,是不如古代的。中国人近代被达尔文主义和它的变体: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洗地非常严重,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主义的变体,也是一种宗教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因为其宗教化,所以很容易发动群众,取得了所谓的“革命成功”。达尔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现在的肯定比过去的进步,未来的肯定比现在的进步”。
其实这个理念纯粹是谬论,信仰它还不如信仰意大利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中国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蛊惑下,盲目地认为自己在思想上也比中国古代进步,其实单从思想上来看,现代的中国人根本无颜面对华夏的那么多祖先,因为中国人不仅仅数典忘祖,从本来的文明状态蜕化到蒙昧状态,还把西方宗教的“恋尸癖”给借鉴过来,不禁让明白人感到一阵唏嘘。
所以,但从中国人被传染了西方的“恋尸癖”,我就可以断言现在的中国已经处于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时代,或者说孔子曾经所说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时代,不幸被我们赶上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饱受蛮族的入侵,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才让中国免于被蛮族同化,而2000年后的如今,孔子的担忧还是变成了现实,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的文化和西方比起来,怎么比都显得很土,很俗,很落后呢,即使那些所谓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如此,这种落后和俗气不是富有不富有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中国人“被发左衽”,现在的中国人的服饰,发型,甚至法律,体制有哪些是沿袭中国的传统的?有哪些不是从西方嫁接的?
关键是,这不是一个“恋尸癖”的问题,要不我们把那具尸体烧掉不就行了吗?最可怕的是,它是思维模式和民族精神的问题,德国人制定一部民法典都酝酿了100年的时间,让中国人从目前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回到传统的思维模式,又需要多少年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篇小文章是说不清楚的。
又不知不觉扯了这么多,不过我有时间胡扯了,说明我又开始有闲暇胡思乱想了,是很可喜可贺的事情,看来,我真不是搞商科的人,倒不是我没有那能力,我觉得在公司金融方面的能力,我在这个MFM项目中的所有人中,至少应该算中上的水平吧,但是我的确没有什么兴趣,也不适合我(尤其是小组作业),不过,好的一点是,我倒是发现了自己对金融市场的兴趣,计划复活节假期时候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