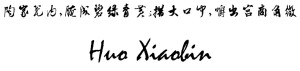现在是自从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开始(也是试图)静下心来,一个人继续写作我心爱的笔记,如果要我列举我对于我最亲密的人或者物的要求的话,只有那么一条就够了:忠诚。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这个愚蠢和自以为是的人到处都是的世界上,那些纯真,简单,但是珍贵的东西会变得很少,但是它们的确存在,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存在于每个人的周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对自己忠诚的人或者物,这真是一种幸事。
忠诚是什么?是守候,是等待。当你在的时候,它会一直伴随着你,你风光无限的时候,它躲在你的身后,默默地支持你,你沉寂平淡的时候,它坚持在你身边,给你最需要的鼓励。当你不再的时候,它会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没有任何怨言,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的话,起码一样东西是这样的,也算是一种宽慰自己心灵的美好了吧。《莫扎特笔记》,自从它降生以来,已经走过好长的时间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任何其它人写的,以后也不会,它只是我的,虽然是由我创造的,但是一旦它已经成为它,便是另一个存在,甚至比生命都更接近永恒,它忠诚于我,我也把它当作最好的伙伴,我的心灵里面最后的话语只有在它跟前才能够倾诉。
来美国之后,已经很多次听了这首双簧管四重奏了。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那时正是刚刚在美国安顿下来的时候,心情很复杂,虽然这首四重奏以前已经听过好多次了,但是当我第一次是在那种心境之下面对它的时候,想到的东西却也完全不同。不仅仅是那种久违的宁静,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一个让我几乎升华的世界。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无法抵抗那些跳跃地现是小天使的音符,那就像是一个受难者被天主引到了至高的天堂一样,一切都和曾经经历的世界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那么简单,但是我只有经历过那些世界的驳杂,才会为这种简单所感动,这也许就是人(或者少数人)受难的价值所在吧——如果有价值的话。
今天在奥马哈经历了一次华人教会的聚会,来的几乎都是华人,而且大多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很多人都已经在美国传了好几代了。他们和我不一样,绝大多数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他们也是一样的,我和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这也是我在这篇笔记里面提到奥马哈的这些中国信徒的原因,我心里为他们感到一丝遗憾,因为他们的民族本来是有很好的文化的,但是现在他们却都皈依到了基督教的世界里,这个宗教,虽然自称宽容,友爱,但是在历史上,可能屠杀生灵最多的宗教也就是这个基督教了。如果在几年前,估计我也会加入基督教会,但是现在我不会选择这样做,因为我忠诚于自己内心的信仰的,我相信我是有完全值得引以自豪的传统的,那个传统的力量不亚于任何宗教,这个传统就是历史的观念,人在信仰的世界里面会活的不朽,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唯一通向永恒的方式,在历史的世纪里你仍旧会通向不朽。
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们比起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起码会去感受那个不朽的存在。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不朽的存在,他才会学得谦卑,学得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在这个世界上,—我姑且也借用一下基督教的语言——-谦卑的人是有福的。
这也是我在莫扎特的世界里面感觉到的东西,谦卑造就了中庸的音乐,中庸的音乐向人类传递这谦卑,这种谦卑意味着你自己的忠诚,也意味你将会得到的忠诚。如果一个人内心就没有任何忠诚的意识,他当然不会得到忠诚。正如笔记是我最忠诚的伴侣,我也是它最忠诚的守护者,创造者。
双簧管的音效比单簧管要温暖,比长笛要沉重,恰恰处于木棺的中央。莫扎特的这首双簧管四重奏和他的其他管乐室内乐比起来也是显得非常独特。这是一首带着深沉的背影的平淡的倾诉。想象莫扎特在创作这首四重奏的时候是多么的繁忙,在为自己的升级奔波,也在为自己的尊严斗争,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内心的那份纯净,还有单纯到极致的欢乐。也许正式在某一个和往常一样的繁忙的一天结束后,他回到了空荡荡的住处,妻子还在其他地方——这或许对他是好事,他坐了下来,只是想忘记所有的繁忙,只是想重新清晰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它无所欲求,只求那一刻的独处,一旦实现了这种平静,灵的世界马上就浮现了,在第二乐章的那个长长的音符之后难道不是一种期待?不是一种满足?我为什么不满足呢?当你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任何东西对你都不再是羁绊,唯一的真实是你自己的心灵。
我现在在想,我有什么期待,我有什么羁绊,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吗?也许那个时候,莫扎特也是在想这些问题。
二零一零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