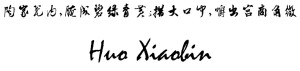这么多年来,我的音乐欣赏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对音乐速度从早年偏爱的“快”变成了现在迷恋的“慢”。一开始,我对马里纳等人的风格非常吹捧,但是到了现在我已经完全受不了这类型指挥家“轻快”背后的“浮浅”,我所钟情的指挥家无一例外不是以“慢”著称,比如朱利尼,切利比达凯,而后者则是最近才开始接触的,可能是因为切氏本来就没几张唱片流传下来,其实几年前我电脑里面就下载了他在EMI的录音集,但是一直都没有理会,毕竟那时还是马里纳等人的拥趸,自然对“慢”地出奇的切氏不感兴趣,只是最近,我发现自己收藏的朱利尼的音乐都已经快听烂了,便想找找其他的和他风格类似的指挥家听听,于是我就发现了一直被我雪藏的切利比达凯。
老一辈的指挥家,除了毫无节操(也毫无特点)的卡拉扬之外,一般都对自己的录音非常谨慎,所以传世的录音都不多,而切利比达凯对录音都到了厌恶的程度,所以他的录音一是不多,而是流传下来的基本都是现场录音,EMI曾经出过两套他的录音集,一套是布鲁克纳全集,另一套就是我现在听的杂集,这套录音里面有他指挥的一些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和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的口味倒是一直都很稳定,那就是芭蕾《胡桃夹子》和交响曲《第五号》,而其他人热捧的《天鹅湖》和第四,第六交响曲我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好多女文青的最爱第一钢琴协奏曲更是好多年没有听了。《胡桃夹子》可以说是人类芭蕾音乐的巅峰,也可以说是莫扎特之后能把童真和忧郁结合地最完美的一部音乐,老柴在这里可以说不输自己最崇拜的莫扎特。而《第五交响曲》则完全符合我的个人口味,因为我所衷爱的音乐,并不是古尔德所嘲讽的“C小调的自恋”式的贝多芬第五或者老柴第六这样的颇为装B的音乐,而是节奏更慢的“田园”风格的音乐,老柴的《第五交响曲》曾被称作是类似于贝多芬“田园”的作品。这部交响曲并没有太过明显的主题的冲突,而且使用了循环主题,整部交响曲除了第三乐章的华尔茨,其他三个乐章的速度标记都是行板,而且所谓的那个“命运”主题在三个乐章中都以不同的形式主导着乐思的发展。这部交响曲,非常像是老柴一个人在夜晚的中欧土地上的沉思,这种沉思既有对俄罗斯风光的回忆,也有对传统的古典曲式的仰望,还有对自己人生境遇的不安,这些复杂的,多维的感觉杂糅在一起,好似“三江并流”一般,构成了一部非常难以解读和指挥的交响曲。
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认为交响曲世界中,老柴的音乐是最难以诠释的,因为老柴不像“强力集团”这些纯粹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俄罗斯风格非常明显,老柴的音乐基本是按照传统的古典曲式和思维创作出来的,但是它们又免不了具有深深的俄罗斯烙印,既有表层次的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烙印,也有更深层次的俄罗斯文化中“受难”意识,所以说一般的指挥家要充分挖掘出老柴音乐中这么复杂的断面,怕是不可能的。所以,老一辈的指挥家,有的基本不碰老柴的交响曲,而尝试指挥的,出来的感觉,用一个形容就是“腻”,基本把里面最重要的俄罗斯式的忧郁过滤掉了,换成了肖邦式的忧郁,这自然就南辕北辙了;而苏联指挥家的指挥不知道是录音的缘故还是乐团的缘故,又感觉太“糙”了,反应不出老柴内心对古典风格的致敬,能把老柴音乐指挥地雅致而不甜腻,深沉而不大条的,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个人,他就是切利比达凯。
这也许和他本人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关吧,他是一个罗马尼亚人,又在德国受的教育和从事指挥事业,所以他对斯拉夫文化有更切实的感触,而又完全融入了传统的西欧文化的体系,这种双重优势让他能更接近老柴音乐的神韵,当然,我所依据的样本也就他在EMI的这几个录音,不过,我听过他的《胡桃夹子》和《第五交响曲》之后,心目中已经不再有其他人版本的地位了,连《胡桃夹子》的名版多拉第版本也不得不退居其次,尤其是最后的“花之圆舞曲”中,切氏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呼吸,那些音符的一张一翕,真的能把人带入一种童话的幻境之中。而《第五交响曲》的演绎,更是切氏一绝,鉴于这部交响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反倒无法用一句两句来形容切氏的诠释了,姑且简单地说,切氏的功力之深,深到能够还原出辽阔的俄罗斯的草原,贵族们的优雅舞步,漫无边际的愁思,还有几乎无法用语言言传的俄罗斯文化和老柴音乐的根:东正教的受难意识。我们放佛能够看到一个痛苦的人在无奈地鞭策自己,在经历了世间诸多的幸福和伤怀之后,在一个彷徨的世界中别无去处,这是一个完全个人的,英雄式的世界,但是这个英雄不是古典式的英雄,而是只有在《塔拉斯· 杜尔巴》里面才能看到的斯拉夫式的英雄和他的无法逃脱的命运。
应该说,是切氏让我重新认识了老柴,甚至是让我重新爱上了老柴,只可惜,他的录音不多,但是细细品味他流传下来的每一个录音,也何尝不是一个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