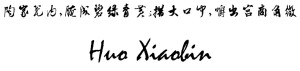摘要:自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事实存在和伦理话题。古代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很多都做出过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他们基本上是反对自杀的,当然有一些人则为之提供了理由和正当性。康德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先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自杀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首先自杀是在自爱的法则下进行的一种行为,但是这种法则并不具有普遍性,故自杀也不具有道德上的普遍性。而与此同时,自杀有是把人当作了工具来使自己远离痛苦,这恰恰是不合乎道德的准则的。最重要的是自杀是对人的纯洁性和绝对性的玷污。所以自杀是在道德上不允许的。
注:本文是本科时写的一个课业论文,先发表于此。
生命的决定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一个人自身的,因为从最自然的角度讲,一个人也可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要他愿意这么做。这是因为人作为一个可以意识到存在于自己周围的多种选择并且从中做出完全出于自己意愿的抉择的个体,完全不同于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其他动物。因为任何一只猫或者任何一只狗,它们的行为仅仅是受制于自己生理的即时的需求。当一只狗感到需要撒尿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它都会毫无顾忌地这么做,但人却不可以这么做。他的行为与其说是服从于生理的需求,不如说是服从于道德的需求,这些需求和前者的不同之处已经不再是完全受自然之力指引而进行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活动,而是他的内心已经具备了“反省”的能力,即它可以自主地而不是受自然之力去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每个行为之前所需要的不是生理的促使而是内心的思索,这种思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决定到底做不做一件事,这种选择的能力只有作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才具有。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自我”处于他做选择时进行心理权衡的中心,“自我”的中心地位往往意味着在“自我”意识十分强大的人的身上往往会发生即使在人类看来都是十分令人震惊而且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件。在“自我” 的意识中人就遵循着自然界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则:自爱。作为一个个体的行为法则,自爱从来便是人们一切外在行为的背后的指导因素,如果一个人爱慕虚荣,他只会做一些有利于修饰自我的行为,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做这些行为,但这往往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他的“自爱”法则已经控制了他的选择,这种选择只有一种,就是一个人的选择服从于自爱的法则。这也导致在“自爱”法则指引下,人的一切行为变成了必然的,而因为如此,哲学意义上的“自杀”也是一个必然的行为。这种行为导致了一个生命的终止,但是却是由这个已经终止了的生命当他存在的时候由他自己实施了这种行为,这在法律上无法清晰地界定,但在伦理学上,这种必然性的“自杀”是否合理却可以作解释的。这时,对自杀的界限便是非常必要的:以自爱为出发点,如果继续自己的生命所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它将会带来的幸福,而采取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便是自杀。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类型的死亡之中区别出自杀行为。自杀的特点在于个体自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生命并不是由自我自愿结束之时,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是自杀了,最明显的对立方式可以称之为他杀。在他杀的情况下,被杀者如果能够继续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会感到无比幸福,而不是无比痛苦,这时他并不是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排除少数的例外),因此死亡者在自杀时所获得的满足与归宿感并不会被一个毫无任何心理准备(即便有)的被杀者所拥有的。但是,自杀者在自爱的原则下实施自杀的行为也许会给他自身带来一定的满足,也许对自杀者自身而言是正当的,但在普遍的伦理法则之下这种行为难道也可以认为是正当的吗?对于自杀的问题,历史上诸多哲人对此问题的探讨很值得我们参考。
早在哲学的童年,伟大的哲学家们就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对于死,苏格拉底似乎已经想开了,所以他泰然自若地死了。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把自然界叫做“可感觉的实物世界”,并且认为自然界是由不变的永恒不动的精神实质的世界也即“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他抽象的虚构出“彼岸世界”并称之为是理念的阶梯,位于这阶梯的顶点是神化了的福﹑善的理念。柏拉图断言,人要想认识真理,就得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沉醉于自我反省,努力去“回忆”自己所谓不灭的灵魂原先在理念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也即“回忆”“回想”的神秘主义理论。它的基础是承认灵魂不依赖于肉体,不依赖于周围的外部世界,信仰灵魂不死。这种学说构成柏拉图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他的伦理学是以他的灵魂学为依据的。他是这样认识死的——“死亡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灵魂习于把自己从肉体的各个部分收集起来,聚集起来,只居住在自己的位置,像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一样,在这个世界,只要她能够,她也如此;——灵魂从肉体的锁链释放出来,”“灵魂的这种分离和释放叫做死”,“只有真正的哲学家在寻找释放灵魂”。他提出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解放”,只有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寻找释放灵魂”,因此,他把哲学称作“习死之学”,研究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在对待自杀的问题上,他同苏格拉底一样,采取不可允许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等待,在神没有召唤他之前,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柏拉图看来,生命的结束是灵魂的回归,然而这样的回归注定是不同于出生的回归。而这样的不同就成就了生命的意义,灵魂被束缚在肉体中形成的混沌的统一体,失去了灵魂的单一的特性,而这样的缺失必须依靠不断的学习(回忆和回想)才能够得到修复。在这样的学习中,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哲学。然而应该来说,生活和哲学是殊途同归的。生活的不断的体悟能够刺激灵魂不断的跳动,即自我反思,而哲学正是这种反思的系统化而已。生命正是要不断的持续这种反思,直到灵魂不再受到肉体的束缚。应该来说灵魂的彻底的解放最终会归于这样的途径而别无他法。然而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解脱的彻底的成功,只有学习充分的生命在受到神的指示以后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生命的中途如自杀,最终导致的是灵魂的被迫的脱离,而影响的却是灵魂的纯度,这样的灵魂将会是痛苦的不完善的灵魂。因此生命不能够随意的被剥夺,自杀是不允许的。柏拉图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于自杀的看法是理念论的,对后世的康德等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不同的是,斯多葛学派肯定了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自杀的正当性。“按照斯多葛的观点,德行就是顺从理性,服从上帝。而理性,上帝存在于人的心灵和意志之中,是他人所不能剥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只有自己的意志可以伤害自己。人若是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自杀也就是正当的了。”[i]但是,即便如此,斯多葛学派仍旧承认“上帝不但做成了人,而且把保护人的责任交给了人自己。就个人来说,当接受了上帝交给你的保护自己的责任时,你就不能辱没和辜负上帝的信任……在他们看来,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上帝。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来自对于上帝的忠诚,对上帝负责,离开上帝的指导,就会做出可耻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行为。”[ii]因此在基本信条上,斯多葛学派仍旧不支持自杀。
而后来神学对于哲学的影响造成了中世纪对于自杀的解释的浓厚的宗教色彩。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一切,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哲学。当时宗教有戒律规定:“不允许为了享受不朽的快乐,或者为了摆脱任何东西,而剥夺自己的生命”。作为中世纪天主教“真理的台柱”,奥古斯丁当然竭力维护当时宗教对自杀的戒律。他认为,法律应当被正确理解,它不允许自杀,既不能杀别人也不能杀自己,因为杀自己仍然是杀人。他在《论忍耐》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没有人应该用心甘情愿的自杀处罚自己。”“因为这是用陷入永恒的罪恶来逃脱世俗的罪恶;没有人应该因别人的罪恶而自杀,因为这是招致他自己更大的罪恶;没有人应该由于自己的罪恶而自杀,因为他还需要自己的生命,用悔悟来治愈这些罪恶;没有人应该为获得我们期待死后的更好的生活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通过自己的手而死的那些人,死后决不会有更好的生活。”奥古斯丁的结论是:“杀父母比杀人要邪恶,但自杀是最邪恶的。”
阿奎那著作里关于自杀的论述很少,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话语中推断出他对于自杀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首先,自杀是违反自然法的。在托马斯那里区分了三种法律:永恒法,自然法和人类法。自然法并不是简单地对事物本性的反应,而是人的理智通过反省事物本性特别是自己的本性而给自己宣布的自然命令。上帝创造人而规定人的本性时,实质上就是给人的心中印下了部分永恒法。人在认识自己的本性时,也就认识这部分的永恒法。这部分的永恒法就是自然法。所以具体地说,自然法早已印在人的心中。自然法是必然的、永恒的,自然法来自上帝的永恒法。因此,自然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托马斯宣称,正因为如此,人一生下来,就受到自然法的管制。等到会运用自己的理智时,人都知道自然法,特别是其中一些基本原则,无需加以论证,都认为是自明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例如“行善避恶”这一条最基本的自然道德原则,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适用,它不可能由于时间的变化、地区的差异、民族的不同,有所减弱或消失。他不仅如此之普遍和永恒,而且又是举世皆知和一致公认。它如同“不能同时肯定和否定”的命题一样,既不需要进行论证而却为大家所接受。因此,“行善避恶是一条首要的法则,其他一切自然法则都以它为基础。”对于行善避恶具体指的什么,托马斯说,第一,“就本性来说,谁都企图保存自己的存在”,这就说明,保存自己的生命无疑是善的,而同时也就意味着杀害生命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应当避免。在托马斯看来,保存生命和避免死亡就是在“行善避恶”这一条基本道德法则上表现出来的第一个具体命令。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托马斯关于自杀的态度:他是违背自然法的,违背行善避恶的第一原则的,是一种没有理性的表现。人一旦通过理性反省自身本性便会遵守这种印在自己心中的永恒法,因而遵守这一保存生命的自然命令。第二个具体命令是“繁殖后代和养育子女”。关于第三个具体命令,托马斯说:“按照人所特有的理智本性,人内在还有一种关于善的倾向,即人倾向于有关上帝的真理和过社会的生活”。自杀者由是观之,既不能完成人性自然的宣布应该男女婚姻和养育子女这一保存人类这个命令,同样也不能作为具有理智的人去和大家一起过集团的生活,关心公益,共同存在。从第三点可以明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痕迹,托马斯也讲过:“人在本性上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注定要比其他动物过着更为合群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人如果自杀,便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不懂得遵守自然法的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便不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和正义的人。
而英国哲学家洛克又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呢?“Since people are the servants of one sovereign Master, sent into the world by His order and about His business,” everyone is “bound to preserve himself, and not to quit his station willfully.”[iii]
首先,洛克认为,宇宙中确实存在“有一位悠久的,全能的,全知的主宰”[iv]即上帝,是它给了人官能,即所谓天赋官能。他说:“我们能够确知有一位上帝——上帝虽然没有给予我们以有关自己的天赋观念,虽然没有在我们心上印了原始的字迹,使我们一读就知道他的存在,可是他既然给了人心以那些天赋官能,因此,他就不曾使他的存在得不到证明;因为我们既有感觉,知觉和理性,因此,我们只要能自己留神,就能明白的地证明他的存在。”[v]其次,洛克从上帝给人予天赋官能,进一步论证人是上帝创造的。他这样写道:“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因此,人的器官组织,天然造得易于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vi]。这就是说在洛克看来,人起源于上帝的创造,而且造得十分合理,使人具有能够进行相互交往的语言工具。正是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根据上帝的指令而降生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存自己,不能随意地终止自己的生命。
上帝的意志是“道德的真正基础”,这是洛克最坚决地坚持的观点。上帝在人面前立下了他的法令,道德生活就是服从此法令,上帝让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们应当服从此法令。但是,人为什么应当服从,他为什么应当感到有义务过一种道德生活呢?他应当服从是出于义务感呢,还是因为他知道某行为是善的并知道他应该为善呢?或者说他应当服从是因为上帝命令他服从,以及因为上帝有权奖赏服从而惩罚不服从呢?洛克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满意的回答。他也没有正视困扰中世纪神学家的更大的难题。道德法令在人们生活起作用,完全是因为它们是上帝命定的呢,还是因为上帝看到这些法令是善的才制定的?上帝是随意选择我们应服从的法令呢,还是他自己在选择这些法令时受他关于什么是善的知识的约束呢?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选择第二种说法更好一些。善不是上帝任性的选择,而是由理性决定的。然而,采用这一选择并假定上帝是受约束的,这就等于限制上帝的行动和选择能力,就等于否认上帝的全能。争论的焦点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如果上帝是随意的,那么所有道德法令就是他的绝对命令,而且他的断言就是他意志的一道命令。没有像自然法这样的事情存在。我们的道德义务决不可能建立在“永恒法和实物的本性”上。所有的法令都是绝对的;可由不依赖于上帝的理性确定并必然为人坚持的自然法只是哲学家思想的虚构。在中世纪晚期思想中,这一论点引起了很有价值的争论,唯名论者整个地倾向于法令是绝对的观点,唯实论者肯定自然法。洛克认为,他不能直接地接受上面两种的任一种观点。他不愿去否认自然法,他接受了自然法,然而,他也不能容忍说上帝是被决定的。整体上看来是,洛克宁愿抛弃自然法概念,而不愿否认上帝的全能。上帝是法令的最后根据。正如洛克所解释的那样,世上必须有一个立法者,而立法者是有权惩罚那些不服从法令的人的。而且唯一的普遍立法者是全能的上帝。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两种观点协调起来呢?在致泰勒尔的一封信中,洛克提示了一个可能的折衷的方法。在那封信中,他把自然法描述为“神法的一个分支”。理性可以感知到,对人来说服从自然法就是善,而正是这种法才是人义不容辞的,因为它像所有其他的法一样,是神圣地被命定的。就上帝强加给我们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自然法也是一绝对的法。这就是洛克竭力呼吁的那种折衷办法。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道德法虽然是神圣地被命定的,但它仍然同人的理性(就人的理性所表现出来的看)相一致,尽管现在看来它是从考察洛克理论的理性主义方面得出的。上帝不是任性地行动,而是根据理性行动的,而他又是自由的。洛克永远不能解决包含在这一观点中的难题,的确,他从来没有着手考察这些难题。我们要想在洛克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前后一致的伦理学理论是徒劳的。他教导我们应当服从道德法,因为它是我们应服从的上帝意志。上帝为了强迫我们服从他的意志,他给服从者以奖赏,给不服从者以惩罚。虽然他直接论述自杀的语言不是很多,但是从他的对于道德的观点来看,人类永远是上帝的仆人,道德的法则就是上帝的法则,他的生命是由上帝决定的,因此自杀无疑是对上帝尊严的亵渎,那么在道德上就是不允许的。可见,洛克仍旧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的。
唯一的对自杀持有肯定态度的是叔本华。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其根源在于,每个人作为意志的一种表现,又是整个意志世界一部分,但作为主体又都有一个依赖于他自己的对象世界,这就是存在于其表象中的世界,即现象世界。对于现象世界,他认为人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现实生活中又无法满足,因而产生“人生即痛苦”的悲观主义哲学。“我们仿佛是四处流浪的孩童,一到这个世界就肩负着原罪的重压。并且正是由于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救赎我们的罪过,才使得我们的生存是如此悲惨,唯有死亡才是我们苦难的终结。”[vii]在叔本华看来,人生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这个欲望满足了又会有下一个欲望。因而,人生的快乐总是短暂的,痛苦却是无法摆脱的。而自杀,是为了从这个苦难的世界解脱出来。每个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和权利,既然人生是痛苦,活着是苦难,既然自杀能够得以解脱,那么,自杀就不应该受到反对,更加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谈到,这个世界一方面是表象,另一方面是意志,意志是世界的本质。“意志是物自体,是一切现象的内容”[viii] “这同一世界,这世界中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客观表现。而意志呢,因为它不是现象,所以不是表象或对象,而是物自体,同时也不服从一切对象形式的充足理由原则;因此,不是任何理由所决定的结果,没有必然性,换句话说,是自由的。……这个对象的普遍性存在和特殊本质,亦即对象中显示的理念,或者换句话说,对象的特性,是意志的直接具体表现。”[ix]生命是意志的表现,自杀是对生命的否定,却不是对意志的否定。“在叔本华眼里,自杀是肯定意志的最强烈的表现……自杀所毁灭的只是个体,而不是物种,更不是意志。它只是在对身体(个别现象)的毁灭之中,连带地否定了这一个体的一切欲求,但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否定意志。在自杀这种毁灭现象中透露出的是意志的胜利,意志的永恒存在,它丝毫不为个体的消亡而有任何损失。”[x]可以说,自杀具有积极的东西——它是肉体的毁灭,肉体的毁灭并不代表着意志的消亡,作为世界本质的意志是永恒存在的自由的物自体。自杀通过肉体的毁灭,通过对生命的否定,达到了对意志的肯定,体现出意志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杀达到了目的和结果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意志的自由并不是自杀所导致的结果,但是,自杀恰恰体现了意志的自由。“倘若反对自杀的理由被认为是正当的,那么,它必然包含了对禁欲主义的承认。”[xi]理想的道德主义者通过反对意志的要求来寻求对意志的征服,而自杀,是通过反对生命的形式来达到对意志的肯定,也就是达到了对意志的征服。
自杀在叔本华看来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杀并没有否定意志,没有否定世界的本质。自杀的个体有权利这样选择,而且其行为的目的和结果并没有构成对世界本质即意志的质疑。世界的本质依然是意志,现象是意志的表现。对于个体来说,自杀是个体肉体的毁灭,个体因此而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脱,摆脱了生命之苦难,人生之痛苦。另一方面,整个人类依然存在,物种依然存在,物自体依然发挥着作用。而且,肉体的毁灭带来的却是意志的永恒,意志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永恒,意志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所以,自杀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反对自杀的理由也是不正当的。他显然是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了,意志和身体的分离并不意味着自杀是合理的,相反,自杀是对于意志的强力的削弱,他没有意识带人类生命中的宗教的意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偏驳的。
康德哲学是德国唯理主义的后代,因此他的论证是理性化的,但是明显受到了前人的诸多的影响。康德主义的立场可以总结如下三点:首先,从自杀和普遍法则的关系角度来看自杀是在道德上不允许的。在康德主义的立场上,一个行为如果是在道德上允许的话,那么这个行为所遵循的原则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则,而不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法则。道德原则作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约束性的法则,它必然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的道德法则在康德看来是先验的显现,因此这一永恒的法则必然对于所有的人和任何的时候都有着强大的和不需要解释的约束力。因此一种行为如果是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话,根据原则的普遍性,那么这种行为必然符合于道德法则,这么一来这种行为所依存的法则也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当然世界上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则的行为是很多的,而一个行为的普遍性应该成为其符合道德法则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无论任何人进行或者在任何时候进行它都不会得到道德上的谴责,而不是在某时候值得同情和赞成而在另一些时候却遭到了众人的唾弃。只有在这种讨论的前提之下,自杀到底应不应该在道德上允许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自杀的限定,自杀的初始的观念是“自爱”。在自杀者看来,自杀所造成的后果和他的自杀在旁人眼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这也应该是所有研究这一现象的人应该有的共识。自杀者当然会认为他应该这么做,否则我们不能设想如果他对于自杀的观念和一般人一样的话,他究竟还会不会自杀。自杀带来的是自杀者生命的结束,这是旁人的看法,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对于自杀者来说也是这样的,也许是因为这一个原因,父母给我们的财富才是最宝贵的,即使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物质财富,但是他们却给了我们生命,这是无论多少的财富也无法比拟的馈赠。一个生命的诞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也许在生物学上,生命无非就是蛋白质和核酸的集合体,人的生命和一棵蒲公英,和一条金鱼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在哲学上人类的生命却有了自己独特的尊严和意义,他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匆匆忙忙地出现又匆匆忙忙地离开的东西。哲学赋予了生命永恒的意义,苏格拉底在他临刑的前夕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将要死去而感到害怕,他拒绝了学生们为他安排的越狱,而是和往常一样和他的徒弟们讨论哲学,而他则说出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和死后将要去的那个世界,究竟哪个世界好,谁都说不定。他明显是第一个对生命进行了理念论的思考的人,对于哲学家来说,生命永恒的意义或许比生命肉体存活的意义更加重要,这才能够体现出人在世界上的独特性。人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也应该时常思考一下自己生命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有时候一般人的对于自杀者的看法是合理的,因为人的本能有时候正是基于人本有的对生命意义非同一般的感悟而出现的,一个小海豹如果自杀的,其它的海豹或许熟视无睹是正常的,可是对于人来说确实可怕的,所谓的禽兽不如。但是对于自杀者却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人是理性的人,简单地说,这里的人是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和将来做的是什么并且明白将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的人,他的行为是受着和他一样的其他人都有的理性的指引的,而自杀这种行为并不是理性的丧失,或者说这种行为和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它不是非理性的后果。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忽然从床上莫名其妙地爬起来,把自己的头颅撞向卧室的墙壁而导致死亡;或者一个人在悬崖上自豪地数自己身上的钞票,但是一阵子狂风吹过,把他的钞票吹走,他由于要去抓自己的钱而不慎失足落崖而亡,这些也是算自杀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杀。自杀的初衷是“自爱”,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行为的法则,至于这个法则是自我的原则还是普遍的法则一会儿会说的。这么看来,对于自杀者来说,他的所作所为,仍旧是从这个原则出发所做的事情。也许他继续活下去的话可能遭受的尘世的痛苦会远远会大于他将在这个世界会享受的幸福,而对于一个珍惜幸福的人来说,这无疑是自杀毫无疑问的先兆,死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没有痛苦也没有幸福,但是继续维持自己的生命的后果却是继续遭受自己很不愿接受的痛苦。这是典型的在理智的情况之下人会自杀的原因,自杀者的痛苦有心灵的也有肉体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心灵的痛苦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试想贝多芬写作海立根施塔德遗书的时候,他的听觉已经开始丧失地非常严重了,而他作为一个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地位却刚刚开始巩固,而在这时候失去听力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并不足以使他有勇气写下这一封著名的遗书,真正的原因是失聪带来的孤独以及对自己的命运的失望, “你们可能认为我固执、癫狂而又孤僻;其实,大错而特错了。我从孩童时代就是善良和温柔的伙伴。不料,这6年以来,我饱尝了耳聋之苦。愚蠢的医师把我的耳朵越治越坏,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是慢性的耳聋了……假若有人在我身旁,他能听见远方传来长笛的声音:而我却充耳不闻;或者有人听见牧羊人在歌唱,而我根本听不见,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啊!……假若,我来不及等到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机会,死亡就来临,那么,不论我的命运有如何乖舛,恐伯也应该认为这死亡来得过早了吧。但愿它再迟些到来。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满足了。因为死亡也许把我从无边的痛苦中解救出来。”[xii]
因此自杀者如果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脆弱的人或者是坚决的人[xiii]就会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死亡,是自爱法则的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杀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姑且假设自杀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如果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便是自杀所依据的法则:自爱在道德上是一种普遍性的法则,那么自杀所遵循也是普遍性的发则,那么自杀就是道德上所允许的了。这里我们要确定的便是自爱能否成为普遍性的法则。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普遍性的法则是不能自我矛盾的,就是不能从这个法则出发能够推论出两个相互抵触的结果,否则它本身便是不可真的。这就是康德哲学中所谓的二律背反。能够推出二律背反的原则是不能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学的法则在它们被运用于现实的领域中是会造成二律背反,说明这些的法则本身在现实中是没有普遍适应性的,同理,自爱的法则如果在全体的道德的领域也同样的推出了二律背反的话,它同样也不能充当这一个领域的普遍的法则。那么自爱的这种原则也不可能成为道德原则所需要的东西。自爱对于生命来说首先是对自我生命的爱护,这一点适合于任何人,自杀者也不例外。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行为只有在这种原则之下做出维护并且延长自己的生命的行为才是善的,因此对于任何的一个人从一般的道德法则来说在自爱的原则的引导之下他无论任何时候要对自己的生命做的应该是延长和改善自己的生命,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生命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人是一个十分看中希望的存在,而生命的存在却恰好给予了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下都不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希望,他即使在那种时候,仍然有可能摆脱掉困境,获得新生。即使是一个绝症的患者,医生所能做的仍旧是尽力挽救和延长他的存活时间,而不会有人让他提前去死。这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但是自杀却使的自杀者向着相反的方向行动,即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心中没有了希望,也不想要任何的希望,死才是他们唯一需要的。简单地说自杀如果是在作为普遍法则的“自爱”的法则的指引下却造成了两种后果,而且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后果:延长自己的生命和缩短自己的生命。于是我们的探讨也陷入了难以解释的困境,这种二律背反说明只有当“自爱”不是普遍法则时才能消解掉这一矛盾。而这么一来,自杀所依存的就不再是普遍法则,它失去了拥有道德合法性的唯一的凭借,因此自杀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能够为一般的道德法则所接受,因此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
同时,从自杀和自我价值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人有其自身的价值。人的价值是那种使人值的活的东西。每个人是有他本身的理性和自主意识的限度来决定他个人的价值的,这种价值是Humanity。它使得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是他超越于一般的动物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Humanity,它对于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应该成为一种终极的法则。这里康德所言的Humanity实际指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来说他们的肉体是唯一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而同时它们的肉体却仅仅是使它们赖以生存的工具,在肉体之中没有理性和自主意识,而人却不同,他有理性和自主意识,这使他成为了人,成为了可以进行自我表现选择和理性思考的生物,而人的这种特性不仅仅是他的存在的依据还是存在的目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使的人对于Humanity所应该做的不仅仅是使用它,它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的目的,人是为了人自身而存在,因此如果仅仅把人自身当作是一种工具的话显然是不尊重人的价值。而在康德看来,如果一个人杀了他自己仅仅是为了躲避外部环境加给他自己的痛苦的话,那么这时他就是在利用自己为一件工具,因为这时候他对自己的肉体的利用的目的不是自身而是在外界,是外界的压力强迫他进行自杀这一种极端的逃避手段,而在此种情况之下人自身的价值显然是处于被丢弃或者置之不理不理的地位,因此这样人自身的意义不能被完全地显示出来。几乎所有的自杀虽然表面上是自愿的选择,但是实际上这种背离了人的求生本能的极端行为的本质是人极其不自愿的最后的选择了,他所遭受的压力或者痛苦有可能是不能够显现的,这种巨大的冲击迫使他采取了自杀这一途径,显然这种行为和他的内心深处的本能是背离的。这时候人为了逃避这种外界巨大的痛苦,只能借助于自己的肉体,这是唯一使自己平静的方法。但是在康德主义的观点中,如果把一个人仅仅看成是一件工具,那么这时候这种行为就是有违于道德法则的,其他没有理性能力的生命姑且不能被随意地当作工具,那么有理性能力的人更不能被当作工具看待了,那么,自杀仅仅把人看成是了一件躲避外部环境加给他自己的痛苦的工具,因此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
第三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杀是对人类纯洁性和绝对性的玷污。人类其所以特别是在于人类的灵魂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说,人的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他本身的灵魂所决定的,人类的所特有的纯洁性和绝对性都是由灵魂来赋予的。宗教上的灵魂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选择了人类作为世界上拥有反省自我和进行思考的能力的唯一生命,他的灵魂就具有了上帝的特质,作为类的人是拥有他所特有的理念的的意义。人类究竟为什么必须在世界上生存并且努力地工作,完全的使用生物学上的本能来解释这么一个问题未免过于强迁,而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从而被上帝罚到了人间,因此说人一生下来就带有了原罪,他必须寻求救赎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纯洁和尊严。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文化的视野中这个主题从来都是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所讨论的中心。在但丁,歌德的文学作品,瓦格纳,马勒等人的音乐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原罪和拯救的主题对他们的创作的影响。在哲学上,康德在重新构架形而上学的时候,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世界现象的世界和本体的世界。在我们看来,也许眼中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所住宿的房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感受的一切,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也许仅仅作经验性的或者是社会学的考察,这些东西显然已经足够了。但是从哲学和宗教的视野中看这一切还显得不够,而历史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关的论述。第一个对此问题做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的是古希腊人柏拉图,柏拉图是以其理念论著称于世的,“对于柏拉图来说,理念是通过概念而认知的东西。那就是苏格拉底用以发现科学本质的概念而不是在可感的世界中原样地反映出来所以这些概念必然形成了第二个或者另一种现实,此现实不同于可感知的世界,它独立存在,这种非物质的现实和物质的现实的关系,如同存在和流变之间的关系一样……总之如同巴门尼德的现实和德莫克立特的现实一样。”[xiv]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现实的东西在于被形式所决定现实的个体,但是却是由形式来决定这些个体的。因此对于他来说,世界万物的四种原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仍旧是以形式因为最终目的的。实在,正由于一个杯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杯子。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它有成为自己的那个时刻,也有结束自己的一个时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实在的个体因为他有出生,他也有死亡。对于一个杯子,它是由某些特定的材料构成的,必然有被废弃的时刻,而重新成为一堆废品。因此实在就在于这些实际存在的转瞬即逝的个体之中,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说实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或者不可信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说杯子这个概念或者人这个概念它们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转瞬即逝的吗?这个人死了,可是人的概念却并没有因此消失,现在并不存在恐龙,可是恐龙这个概念却存在于任何一本权威的字典之中。因此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是永恒的。柏拉图终其一生去证明和论述存在的合理即概念世界。对于实在的确信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即使我们确认了眼前的东西就是杯子,但它实际上又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视野和经验所能够涵盖的了。而实际上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都无法洞见真实的存在,存在这时候需要人的信仰的力量,也就是说只有信仰才能够使人类经验到他的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一个人能够感觉到杯子的存在,但是感觉不到杯子这个概念,但是他仍旧相信这个概念的存在。
与此同时,他同样把人分成了两个人,灵魂的人和肉体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人类是能够寻求其永恒的存在的,当然人类的永恒是取决于他的灵魂的,绝对不能够依靠其肉体,也正是它使的人能够在一个瞬间即逝的实在世界之中思考生前死后的事情,也就是说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事情,也是灵魂的事情,不仅仅是在短暂的人生中肉体的旅行,也是独立的灵魂寻找永恒的归宿的历程。在人类的肉体的身上还有着灵魂的决定因素,它使的人类不能够随意处置自己的肉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注定的东西(Obligation),如果在宗教的意义上说,他需要获得救赎,这种救赎最终使人回到了他一开始是的样子,回到了他和上帝一同沐浴崇高的光芒的时日。在这种意义上,自杀如果不是为了救赎,而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这样,自杀者不仅仅不能获得拯救,而且会永远地拥有原罪,这种他摆脱不掉的原罪即使在他死后仍旧会纠缠着她,肉体的解脱并不意味着灵魂的解脱,只要在他临死的那一刻,对灵魂的愧疚感仍旧向他即将遭到的痛苦一样强烈,那么他的灵魂就会永远遭受痛苦。瓦格纳的歌剧由于触及到了这种人类生命中极其重要的理念的原则而使的它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一种哲学的魅力,他对于拯救和生命的思考几乎革命般地使我们能够艺术地洞悉生命的本质以及拯救的崇高的意义。他写有一部歌剧叫做《飘泊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ander),它讲述了一个荷兰船长由于受到了上天的诅咒而被罚永远在大海上驾驶着有血红色大帆、漆黑色船桅、看来气氛诡异的船只(即幽灵船)在大海上没有目的地航行,每七年才能上岸一次,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爱他的女子的话,才能解除诅咒,得到救赎。当又一个上岸的时候来临时,他遇到了挪威船长达朗德,荷兰人问他可否邀请他到家中小憩,他会有金银相送,达朗德满口答应,接着荷兰人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问达朗德家中是否有爱女,有的话可否引荐,促成一段姻缘,这样一来自己身上的诅咒就可以解除了,达朗德也满口答应了。而几乎于此同时,达朗德的爱女森塔在家中发现了这位受到了诅咒的荷兰船长的画像,唱着叙事曲说出了他的命运,最后发誓她就是那个解救荷兰船长的人。当荷兰船长和达朗德回来的时候,达朗德作为引荐人,让自己的女儿和荷兰船长见面,两个人一见倾心,荷兰船长相信这就是那个可以将他从诅咒中解救出来的女子,而森塔则热情地宣布,她将向荷兰人献出永恒的爱情和忠贞,来征服撒旦的魔咒。但是一直爱恋着森塔的猎人爱立克则在此之后苦劝她不要冲动,应该回心转意。森塔告诉他她心意已决,婉言谢绝了爱立克的求爱,这时候荷兰人出现,他以为森塔已经变心,背叛了拯救他的誓言,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再次起航,继续他飘泊的生活。森塔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没有改变,爬上了岸边一个陡峭的岩石,在幽灵船即将远去的时候,纵身跳下了大海,自杀徇情,与此同时幽灵船在风暴中沉没。在一阵汹涌狂涛之后,只见荷兰人和森塔二人的灵魂相拥升出海面,飞向天堂。荷兰人终于得到了救赎。
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之中得到一些关于永恒的信念和对命运的感悟,他对我们最强烈的冲击在与一个人的肉体是通往永恒的桥梁,他不能在没有得到救赎的情况下自杀。每一个人只要当他思考永恒和他自身时,都会对这种强烈的命运的力量抱以神圣的敬畏。在这种极富神圣气息的环节中,人的痛苦来源于他的原罪(漂泊的荷兰人因狂妄自大而得罪了上帝),他的罪恶导致他在人间做无休止的无意义的工作(如荷兰人驾驶着幽灵船在大海上漂流,这和加缪所热衷于引用的西西佛斯的神话是相似的)。而这恰好是他的命运。那么人的命运和他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呢?他的生命是服从于他的命运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能服从于他的命运,而这恰恰使人生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色彩,他就像渺茫的宇宙一样空洞,但却同样像渺茫的宇宙一样令人敬畏,这正是人不能妄动自己生命的原因。他必须相信命运,他必须相信在转瞬即逝的世界之中,仍旧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命运,他只能在一生中孜孜不倦地寻求救赎才是其生命的意义所在,而这种意义使生命蒙上了一层神秘却纯洁庄严的色彩,它使人的命运在它结束的时候最终完成,而它的灵魂也得到了救赎,飞升天堂,因
此无论什么时候以自杀的方式干扰这种神圣的历程都是对这种神圣性和纯洁性的玷污和干扰。
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Obligation,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通过努力甚至受苦而重新寻找到自己生命的纯洁性和绝对性,从这一个方面来说,人的生命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它的出现是一种奇迹,而一旦它已经出现了就注定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命运,他的一生是在命运的支配之下进行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是他最合适的生活方式,不仅仅基督徒有修行的习惯,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通过苦修来达到拯救自己灵魂的目的,早期的佛教徒通过在深山老岭之中修炼来最大限度地抑制自己的在尘世的欲望,人的尘世的欲望(肉体的)和灵魂的升华(精神的)是此消彼长的,只有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肉体的欲望才能真正达到灵魂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之下自杀无疑使这种灵魂的升华过程嘎然而止,它或许出于自爱而为之,但是这种自爱而导致的自杀依旧是受着欲望的引导而或许完全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快感而为之,这是不能获得生命的纯洁和绝对性的。
在诸多的论证之中,康德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对于以前的观点的否定,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重新系统地发展而来,而这样一来也使得他的观点更加有力。无论是谁的论证,我们都是有理由相信,即使今后有谁愿意重提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仍旧会和前哲们一样。
[i] 罗国杰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78页
[ii] 罗国杰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78页
[iii] Victor Cosculluela ,1995:the ethics of suicid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5页
[iv]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9页
[v]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14页
[vi]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3页
[vii] 《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柯锦华,秦典华,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25页
[viii] 《叔本华人生哲学》.叔本华著,李成铭等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381页
[ix] 《叔本华人生哲学》.叔本华著,李成铭等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382页
[x]《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黄文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5页
[xi]《叔本华论说文集》第440页,范进,柯锦华,秦典华,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xii] [英]琼斯:《贝多芬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xiii] 自杀并不是脆弱者的专利,因为有时候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并不少于杀另一个人
[xiv] [德]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M]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72页
参考文献:
罗国杰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范进,柯锦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秦典华,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黄文前.《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英]琼斯:《贝多芬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德]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M]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Victor Cosculluela.the ethics of suicide ,New york ,1995garland publishing
Richard Wagner .Der fliegende Hollander(CDs &Libretto),Decca,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