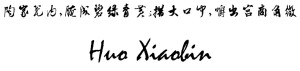3,个人独立思想的来源及其本质
前面我们谈到了个人独立思想提出的原因,和个人独立思想实现的条件,从中可见,福泽的个人独立思想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再探究一下这种思想的来源问题。而从这些来源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泽瑜吉所谓的个人独立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中关于个人的平等、权利所存在的不同,从中认识福泽所谓的个人独立的所具备的本质特征。
3.1,个人独立思想的来源
我们不难看出,福泽谕吉的个人独立明显具有西方启蒙思想的色彩,但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自己到底有没有受过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福泽谕吉个人独立思想到底来源于何处?是有西方思想的作用,还是仅仅是他个人的独创?实际上两种因素都存在。现在外界一般都认为他的独立思想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日本著名的福泽谕吉专家远山茂树在他的《福泽谕吉》之中持这种观点;“不难推知,《劝学篇》曾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全书着力宣传如起首所说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种主张四民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我基本同意远山茂树的观点,因为福泽早年热衷于于西方文化,学习并且精通荷兰文和英文。在写《劝学篇》之前已经有过丰富的出洋考察的经历,他曾经去过美国,欧洲,对西方的风俗,政治体制作过详细的观察。他曾经写过许多介绍西方的书籍,比如《西洋事情》,《西洋导游》,接触过其他的介绍西方的书籍(比如当时在日本十分流行的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些书籍大都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而不局限于介绍西方的科技成果。从这些著作的完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福泽谕吉的个人独立思想必定受过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然而,仅仅是西方思想就完全可以解释福泽个人独立思想的来源了吗?远山茂树和其他福泽谕吉研究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我们答案,然而我们可以从福泽晚年的自传之中寻找到。在这部《福翁自传》之中,福泽谕吉详细的回忆了他的早年的岁月,在许多事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泽谕吉自身的性格之中便具有独立思想的气息。早年的福泽谕吉最不能忍受的便是当时日本严重的门阀制度,并且认为他的父亲一生悲剧的原因就在于门阀制度。他小时候从来不相信鬼神,还干过踩踏神符,给神祠之中的圣物掉包的事情,这在当时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福泽能做得出来,恰恰说明他自身便有一种自发的独立意识,对封建的观念有天生的反感,这些后来在他的《劝学篇》许多篇章之中都反映出来了。比如,在第二篇之中,他对武士和平民的等级划分进行了批评,说“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1],第三篇之中提到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培养了国人的奴性,导致本国人见到了外国人也忍受巨大的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2]这些反对门阀制度,提倡个人的人格从等级人伦中解放出来的思想都体现了需要个人的独立精神才能得以实现,实现了个人独立,就不会再有社会等级的区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而人民也不再在受国家愚民政策的折磨,见到外国人就会懂得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这种个人的独立最终能促进了国家的独立。因此,如果把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仅仅归因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的话,显然有失偏悖,他的性格和生平对于他的独立思想的产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3.2,福泽谕吉个人独立思想中的国家意识
中国对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其中的启蒙意义,比如赵乃章在《论福泽谕吉的民主启蒙思想》之中特别强调福泽谕吉是日本文化之中的“伏尔泰”,并且把《劝学篇》之中的独立思想和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等启蒙概念联系起来,在评论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的时候不自觉地是在西方的思想语境之中进行评论。事实上,中国甚至许多日本的学者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福泽谕吉《劝学篇》之中的个人独立思想的,似乎只有在西方的概念之中才能够最好地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中国如此,西方更没有理由不是如此,布来克在她的《福泽谕吉著作研究》之中,说道:“就象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哲学一样,(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治以后的启蒙运动致力于教给其国民新的学习方法,对于人和他在自然之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3]。诚然,这是一种解读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也不是最合适的方式,正如上文我所分析到的,福泽谕吉的个人独立思想尽管受到过西方的影响,但是更大的程度上,这种个人独立的思想是来自于他自身的经验所激发的他对于日本的固有的传统的反思。如果从上面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个人独立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忽视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其实从以上对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的分析之中我们不难感觉得到,破除封建观念,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这是对于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追求。如果完全是从西方启蒙思想的语境之中来看待福泽所提倡的平等,那么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当作是福泽谕吉用来对抗封建主义,追寻个性解放的武器,但是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些。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恰恰忽视了福泽谕吉思想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提倡平等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吗?仅仅是为了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突出日本内部的剧烈的阶级裂痕吗?
并不是这样的,福泽谕吉考虑个人独立从来都不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或者单纯的反封建的角度来考虑的,他是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罗华庆比较清晰地阐述了这种关系:“福泽谕吉主张平等独立的观点,其内涵随其外延的扩展而愈益丰富和升华:由‘天赋人权’决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由‘主权在民’所决定,人民与其代表自身的政府是平等的;‘由不同国家的主权分属不同国家的人民所’所决定,国家和国家是平等的。在这里,主张个人平等自由的‘民权论’,与主张国家独立自主的‘国权论’,很自然地揉和在一起。”[4]所以,尽管福泽谕吉提出的独立,进而平等的观念,是和西方的启蒙观念一样的,但是在日本特殊的背景之下,它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内涵。在福泽这里,独立和平等更多的是一种人类的普适的价值观,而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之中是有不同的效应的,在日本,福泽把它们看作是实现日本国家独立的基石,所以即使是在主要论述个人独立的《劝学篇》之中,背后仍旧有着浓厚的国家意识。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以后所写的《文明论概略》一书,可以说,《文明论概略》是对《劝学篇》之中没有来得及谈的问题的继续分析。
远山茂树也指出,即使是福泽谕吉在酝酿《劝学篇》这部旨在宣言个人独立的著作的时候,仍旧一直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当福泽谕吉提出了个人的独立的时候,马上便写了《论尊重国法》,《国法与人民的职责》来限制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远山茂树说:“第六、第七这两篇的主旨似是劝喻人民承担遵守法令的义务。”[5]第六篇就是《论尊重国法》,而第七篇就是《国法与人民的职责》。在第七篇之中,福泽谕吉说:“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但是“用实力对抗政府,…….,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划。”[6]“福泽在促使实现个人独立即人民的权利方面,是倾注了相当的心血的。”[7],但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上,“他把‘主张人民的权利,用真理说服政府’,视为上策中的上策。”[8]因此,个人的独立是以政府的完善为条件的,而不是象西方的启蒙思想那样认为个人独立意味着有权推翻政府,这在福泽谕吉看来是很不明智的。
在基莫斯(Earl H. Kinmonth)对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之中的自由和独立所写的《重新思考福泽谕吉》(Fukuzawa Reconsidered)一文之中,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看法。正如上文所说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福泽谕吉《劝学篇》之中独立思想和对于封建观念的批判归结于他所受的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并且因此而成为了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基莫斯几乎在他的论文之中全部推翻了这个已经普遍被接受的论点。“即使有一些突破,但是这种对于福泽谕吉的研究方式仍旧大行其道。甚至那些宣称对于福泽谕吉的思想进行重新评价的人都落入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而没有仔细地考察相关的证据。”[9]他反对把福泽谕吉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归结为西方启蒙文化尤其是英美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因为福泽谕吉的独立和自由所暗示和指向的完全和英美近代启蒙思想不一样。在杰佛逊那里,对于政府的反抗是人类基本的权利,民众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是在《劝学篇》却找不到甚至是这种暗示。而在另一方面,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虽然里面处处说到民众,而且发行量非常大,但是它的阅读对象基本还是当时的武士阶层,这也是福泽谕吉所处的阶层。《劝学篇》的主旨是鼓励人们一心向学,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财富和名望,最后仍然是肯定现实的政治,甚至鼓励人们通过学习获得财富和名望之后去从事现实的政治,这种思想完全和启蒙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阅读对象大多是武士阶层,这便成为了鼓励武士阶层一心向学,进入政治,以改变自身现状的教科书。在基莫斯的考虑之中,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不仅仅不能使他成为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表明他是在为特定的阶层所服务的。这个观点相对于大多数的观点显得非常非常激进,尤其是它将独立的思想局限于武士阶层之中,但是它在绝大程度上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正如基莫斯所说的:“他(福泽谕吉)很少脱离幕府的观念,尤其是武士阶层;而他对于‘权利’追求是有其他的目的的,并不仅仅是《劝学篇》的目的所在;他对于权利的观念是来自于十八和十九世纪更加保守的观念;本书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武士阶层发出需要独立和权利的呼声。”[10]
其实一旦福泽谕吉代表了武士阶层,那么他也就代表了当时日本的国家和政府,因为即使到了明治时期,日本国家的统治主体还是过去的武士阶层演变而来的。基莫斯的这一观念,更进一步证明,在《劝学篇》之中福泽谕吉所追求的人人独立和人人平等的思想并不是他真正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东西是这种独立和平等实现之后的一种国家状态,人可以通过一心向学创造财富,获得名望,但是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扶助政府的运作。即使是在个人的完善这种事情上,国家观念也都是贯穿始终的。显然,仅仅一部《劝学篇》福泽谕吉还不能完全充分地表达出他的思想,所以在分析完福泽谕吉的个人独立思想之后,最后,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谈一谈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在福泽的文本之中有什么样的关联。
3.3,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福泽关于个人独立的基本思想,可能我们立刻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在福泽那里,个人独立的实现是目的呢,还是仅仅是一种手段,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无疑:个人的独立并不是福泽唯一所关心的东西。因为福泽谕吉目的是在追求论述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国家的独立。当然这个问题只能以个人的独立为基础和前提。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之中并没有对国家独立这个问题作太多专门的分析,但是我们从他对于民众和国家的关系之中能够辨别出他对于国家独立的提倡和向往。
因为之前所提倡的都是个人的独立,而每个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会和社会,国家发生关系,可以说个人的独立与国家的状况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种独立的精神如果继续放大到国与国之间,那便是各个国家之间都是自由独立的,虽然国与国之间有贫富强弱的不同,但是都有平等的权利。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福泽谕吉说这些话的时代的状况,当时世界上西方国家纷纷崛起,成为强国,但是日本等东方国家仍旧处于落后的社会和观念之中,两者一旦发生接触,日本立刻便陷入了不利的境遇,所以日本才更加迫切地需要国家独立,否则就容易陷入被西方国家欺凌,奴役的境地。而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必须先改变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福泽为什么在《劝学篇》之中不厌其烦地谈论暴政的问题,其实这便是影射当时的日本政治状况。
在《劝学篇》第六篇《论国法》之中,福泽谕吉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谈到了暴政的问题。政府和人民并不是谁统治谁,谁敌视谁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可能指引日本走向近代化,一方面政府需要发挥它对于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民也要有独立的精神,正如他说的:“政府活动犹如体内活动,人民犹如外界刺激,如果把这些刺激去掉,只凭政府力量去活动,那么一国的独立就一天也不能维持。”[11]因此必须维持二者的平衡,那么就需要需要法律来维持。国民一方面要建立代表自己权益的政府,另一方面要严守同政府的契约,服从国法,接受政府的保护。法并不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民众的权威才建立的,而是民众自己为了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制订的,进而建立政府来代表自己,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执行事务,制裁恶人和保护善人。但是一旦政府已经建立,国民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律。自古以来的政府,并不是千人一面,有实行仁政的政府,也有实行暴政的政府。当国民面对政府的暴政的时候,一般会有三种举动:一是屈从政府,这不是一种好的办法;二是用暴力对抗政府,这往往造成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对社会有很大的破坏,所以也不是一种好的办法;第三种才是上策,即坚持真理,舍身斗争。“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已由此论阐明,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12]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福泽把社会变革的希望是寄存于社会有识之士的身上的,希望通过他们的社会活动促使现状的改变。
因此,社会活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人作为人的意义不仅仅在与自己可以养活自己,自力更生,还在于他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应该在社会性的活动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人要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要尽到自己对于社会和国家的义务,而且有所得就应该想到贡献于社会,而不是仅仅想着一个人享受;另一方面呢,我们不仅仅要着眼于现在,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社会活动还要为后代作出示范,使文明得以继续发展。但是这些的前提还是自力更生,因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只有短处,没有长处,所以现在只有学习西方的份。但是如果一直学习下去,文明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福泽实际想说的日本应该努力在许多方面超越西方,比如技术上比西方进步,自己的人可以去教西方人学问,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日本真正强大,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
从上述福泽的关于个人独立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泽的思想到这里已经从单纯的个人的独立过渡到了国家独立的层次上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实现个人独立,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国家独立才是最终的目标。正是因为这样,他在撰写《劝学篇》的同时,开始着手撰写他的名著《文明论概略》,全文的脱稿比《劝学篇》还要早一年[13]。在《文明论概略》中。他着重从文明的角度阐述国家的独立问题。
[1] [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 劝学篇,10页,商务印书馆,1992
[2] [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 劝学篇,17页,商务印书馆,1992
[3] Carmen Blacker: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 A Study of Writing of Fukuzawa Yukichi , Cambridge Press,1954
[4] 罗华庆: 福泽谕吉《劝学篇》中独立思想的积极意义,《历史教学》1992年第3期,5页
[5]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译:福泽谕吉,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 劝学篇,17页,商务印书馆,1992
[7]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福泽谕吉,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8] [日]远山茂树著,翟新译:福泽谕吉,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 Earl H. Kinmonth: Reconsidered Fukuzaw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7, p677
[10] Earl H. Kinmonth: Reconsidered Fukuzaw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7, p681
[11] [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 劝学篇,20页,商务印书馆,1992
[12] [日]福泽谕吉著,群力译: 劝学篇,42页,商务印书馆,1992
[13] 从福泽给友人岛津佑太郎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该书完稿于明治八年(1875年),而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到,最初的构想是在明治七年(1874年)二月,而《劝学篇》第十七篇却是完稿于明治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