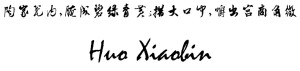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一)
在人间的某处。一人,其母。
及此人长大,母曰:“你该去找那了”。
于是他开始了寻找“那”的历程。
一日,遇一长者,问:“我在哪?”,答曰:“你在这。”遂去。
又一日,遇一贤者,问:“我在哪?”,答曰:“你在这。”遂去。
复一日,遇一智者,问:“我在哪?”,答曰:“你在这。”遂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及此人老,再无力行旅之时,瘫坐于地,自言自语道:“我在这尔。”
(二)
自西人有哲学近2000余年间,最常为人道者当属最早被誉为哲人之苏格拉底,他提出了一条自见诸世人以来便引发了无数争论,诠释以至于今的论题:人的主体性。然而他也是最早将“彼”和“此”分离的人之一,他认为只有存在于自然“彼岸”的永恒的灵魂和“全知”的神,才创造了世界。因此从哲学史的开端,人类便是被抛弃于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非洲或者美洲或者南太平洋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个从未受过人类文明(包括自有思考和哲学以来的人类文明)影响的人的话,那么他们有很大的可能会不能适应时间的存在,时间是现代人类所创造的制约自己的一生的一种认知形式。在从没有过时间观念的原始人或者未开化人的眼中,他们生活在当下,他们要思考的东西只是当下,如果给他们时间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他们可能就会死去,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便被抛弃到了另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了。然而,早期的人类却在慢慢地为自己寻找这么一个世界,有一种关系是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究竟是两个世界的划分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导致了两个世界的划分,但是无论怎么说,自从人类一开始思考,他们便从不满足于自身,但又从不试图去认识自身,或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认识你自己”是一条多么具有智慧的论断,他们只是将自身的命运寄托到了另外的主宰者身上,并且由此产生了“意义”这个东西。若论到人,意义之意义在于他的行为对于某种法则的契合,但是这种法则却远远不是自身内部的规定,而是全然外在的:有宗教的法则,也有传统的法则。若论宗教式的法则,我们必然意识到了人类早期的困惑与脆弱,正由于自身不知道自己为何物,正是因为自身利益感到了一种生存的困境,早期的人类遥想一种在人类之外的神的保护,是为最早的宗教的发端。宗教的形式是一种典型的且最广泛的人类对于自身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我及其控制自我者是相分离的,也是因为此种分离,自我的意义才能够显示,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意义在这个时候暴露的是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于责任的回避,这种回避待我们说完历史的法则之后将会更加的明显。与西方诉诸宗教的习惯不同的是,中国人习惯于将意义诉诸历史,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没有宗教而又如此具有现代意识的基因,可能便是因为中国人坚强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与西方的宗教感可谓是殊途同归,都直接地导致了现代的最大的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呆会儿将会论及。
再回到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话说中国人喜欢历史,更喜欢写历史,早有《左传》,《春秋》,微言大义,已经成为了公认的经典,晚有《资治通鉴》,在这种对历史的极其大的重视之中我们明显可以窥视到中西传统文化在表面相异之下的共同之处。中国人写历史明显不是单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最直接的文化信号在于对于家族的传承的重视,我们的祖先不象西人,寄托自身命运于上帝,并且认为荣升天国,享受永久之极乐乃奋斗一生之目标与最大的幸福。这种观念在中国则并不普遍,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一下子就把个人死后的事情给排除掉了,但是中国人仍旧不得不考虑意义的问题,既然身后之事无从谈起,正是:“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是假如要生发个人之意义,那就只能诉诸血脉传承,中国古语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中透露了两点信息:第一点信息的关键是“不孝”,显示了对于祖先的尊重,第二点信息的关键是“无后”,显示了对于血脉传承的尊崇,仅仅八个字,却描绘了一个完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景,这个图景不就是一个永恒的图式吗?我想若要生发,此八个字完全能够成为一篇煌煌巨著,然而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只能简而又简。话说在这种历史图景的构想之下,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便也同时被构造出来了,而且其效果不亚于西人之宗教世界,西人自恃宗教之崇高无比,且那种天堂极乐也由自己身后来享用,全然乃个人意义上的构想。若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眼中真乃狗屁不如,因为信仰天堂原本便是一种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信仰之谓,为信奉所可能没有的世界也,正因为这个世界可能有,可能没有,才会有信仰的出现,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便是一种无本之木,无果之花的行动,哪如家族遗传,有了儿子,血脉便不至于中断,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永恒。在这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盖从古至今,由外至内亘古为有过之者。放大到整个中国历史,史家著史,亦为此心也,历史之中自有中华民族的根本基因,两千年史家笔耕不辍,不断著史,即便到了国破家亡,沦为亡国奴的境地(如元清两朝)仍旧不忘祖宗之法,不忘紧紧抓住这根救命之绳,再次证明只要中华历史观念不断,文化基因就不会断,曾经统治过中国的蒙古人现在龟缩于我国北方一隅,而满人则早已经不知所终,灰飞烟灭,而我中国人仍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可见历史观念之于中华民族的关键作用。
前文所说,中华历史感与西人之宗教感乃殊途同归,那是什么样的殊途同归呢?在前面的分析之中不难发现,西人诉诸宗教,乃求永恒的的平静,而中国人诉诸历史,时间感则更强,仍旧力求永恒,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土著人问题。无论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其整个社会文化都是在一种强大的时间观念的支配之下进行,时间观念的产生带来了人对于自身的局限性的困惑以至恐惧,这种恐惧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不同的人群之中人们选择了不同的消解恐惧的办法,对于人类进行简单的考察,主要有三种方法可以消解这种恐惧。
其一乃西人之宗教法,设立一个人间之外的世界,宗教的法则一方面为人间的行为设立一个神圣的准则,更主要的是为被时间所困扰的人类摆脱时间的局限而在永恒的天国之中把时间给消解。
其二乃中国人之历史法,仍旧立足于现实世界之中,但是不仅看重于一个人或者一代人,而且看重于血脉及基因的传递,一代是不得不受时间的局限的,但是代代人之间便可以把时间个消解掉,达到永恒。
以上二法,其实可以合二为一的,就是先设立时间,然而又寻找办法去把时间再消解掉,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折磨的过程,但不能否认这种自我折磨是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当人们诉诸宗教或者历史的原则的时候,是刻意在忘掉自我,其实是忘掉自我局限性所带来的无限伤痛,在一个外在的宏大的世界之中寻找自身的意义。按照现代哲学的说法来看,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被抛弃状态,即当一个人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便是处于一个短暂的受限的世界的,于是他必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来消解这种时间所带来的困惑,于是他的一生都在寻找“彼岸”,他在此的目的便是去寻找“彼”,但是这种对于彼的寻找在现代人的观念之中却又成为了一种尴尬和困境。
而第三种方法则是从源头上消除了因为时间的观念而引起的困惑,那就是选择不要时间,正如那些非洲土著所做的,既然没有时间,那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那就没有困惑了,他们只是生活在当下。但是那些生活在当下的人却没有我们现代人心目之中的现代文明,在此看来,时间观念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似乎更加明显了,但是其因果关系我却不能因此而妄加揣测。
这些观念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还是有其人为性,我更加赞同后者,正如一种理论认为希腊民主制度并不是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一样,而是因为那些有权决定国家的政体的人选择了民主,而没有选择专制。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正好相反,那么在对时间的态度上,西人与中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选择了时间并且与此相伴的困扰,但是在对如何消解时间的方式上,两者却做了非常不同的选择,西人选择了宗教,而中国人则选择了历史。土著人则完全不选择时间,他们的思维永远停留在了当下的状态之中。而我们现代人,在消解掉时间之余亦同时面临了因此而带来的其他困惑。
(三)
由上文可知,现代人之所以意欲消解时间,在于他们陷于一种时间所造成的痛苦和烦之中,及其对有限性的困惑,然而当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不同的道路—无论宗教的还是哲学的—来从永恒之中把自己从当下的困境之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这种解脱本身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时间的消解在于当下的消解,这种消解又在于使用一个彼岸来对抗当下的自我,在这时候如果自我意欲摆脱掉有限性的困惑的话,那么就会全身心服从于那个自己所设定的范式之中的规则,比如历史的范式或者宗教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的心灵就离开哲学史一开始所说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渐行渐远,俗语曰,“物极必反”“水满则溢”,自我在寻找摆脱有限性的困惑的过程当中却把自己完全依附于上帝或者历史,其结果是逐渐明显的自我的缺失。说到自我的缺失,当亦为近代哲学历史之上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我在此并不想引经据典证明相关的论述的存在,因为我们仅仅从上文所论述即可作出相关的推论,这似乎又涉及到了人类本身的弱点,如果一个男人知道这类弱点的时候,他肯定会说:“只有女人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无论女人还是男人都会犯这种错误,因为那是一种人类“依靠”的本能。人自身不单单只有其在时间之中呈现的局限性,人自身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然而只有古代的少数人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人有许许多多的属性,人有许许多多的需求,但是似乎我们的祖先并会去考虑这么多。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其实不在于对于时间的意识,而在于对自身的认识,这种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所极其重要的部分,对自我的认知与肯定必然引发了对自我表现的信心和改变世界的动力。但是随着人类依靠自己所设定的宗教观念或者是历史观念时间过长,人类倾向于把自己整个地依附于这种观念之上,那么对于自我的观念也便会被不自觉地依附于宗教或者历史的准则,这种依附往往有巨大的后果。无论西人还是中国人,它都带来了自我意识的缺失,而一旦缺失了自我意识,那就意味着人类开始进入了另外一种心灵的困境。这样当他试图通过外在的彼来消解自身由于有限性而带来的困惑或者不安时,却同时陷入了由于自我表现的缺失而产生的另外的困惑和不安。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自黑格尔之后便出现了反传统的哲学的浪潮,君不见著名新派哲学家尼采高乎:“上帝死了”,盖发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心灵中的声音,尽管由于言辞激烈,尼采被诸多人所垢病,然而从此以后人类的哲学就再也没有回到传统哲学的那种状况。而中国的情形比较特殊,自西方近代以来由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至今,中国人内心便没有停止过自卑与媚外,虽然1949年以后中国人在政治上便不再是亡国奴,然而直到今天在精神上中国人仍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亡国奴。直到如今,中国人在精神上仍旧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故而到如今西方人陷入了困境,国人亦陷入了困惑,是真的困惑,还是单纯地模仿,避免显地老土?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亦在这种情况之下莫名其妙地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了。
不管怎样,传统的观念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来分解,总之我们终于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而且这种困境弥散在了现代哲学的骨髓之中。当人类又一次习惯地寻找历史或者上帝的时候,终于有人站了出来,似乎不经意地说道:“你在这儿。”这其实是一种无奈,因为他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把人类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赖以存在并且寻找人生意义的外在法则重新给消解掉了,人类重新回到了原点:享受在时间观念这一前提之下的困惑与不安。
先前的人类只知道“我要往彼”。而现代人则只知道“我在此”。 “我在此”似乎从言辞上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论断,可以说这种论断无论什么时候作出都不会是错误的,因为“我在此”或者“你在此”这种命题的背后隐藏着由于时间观念而造成的外有的“范式”的消解,如果人类这时候仍旧有很强的时间观念的话,他必定会陷入另外一种困惑,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是存在的。然而他所能确认的仅仅是当下的自己,不能溯及既往,也不能开启未来,如果人是一个立体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人只是一个藐小的点而已。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人类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不象原始人一样不知道,所以人的困境便由此而彰显,这是人类的一种现代病,这种病与非洲的原始人的生活状况有相似之处,但是区别在于后者并没有时间观念,而前者之所以有病是因为他有时间观念,却发现自己只能考虑当下,那么那种依附于必须由人所设定的永恒的意义便不存在了。
因此,这便是人类的困境了,究竟怎么能是人类象摆脱上一次困境一样摆脱这一次困境呢?我想这将会是一个有趣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