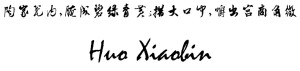感物伤怀是中国诗歌之中的一个非常普遍而且常见的范畴,它的意思是:当诗人见到一个特定的景物,由于景物特定的意义,心中某种固有的潜伏着的感情能够借此得到抒发。而这种感情是一种怀才不遇而感慨身世,忧国忧民之情,物在这时候已经不单是一个物了,无论它是一朵绽开于原野之中的花朵,还是戈壁滩上的落日,抑或是历史的遗迹,在此时的诗人的心中和眼中,不单单是代表一种有着自然美或者外在情调的东西,而是成为一种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氛围的物体,而这种特定的氛围与诗人心中深藏不露的情怀相合,最终物情相融形成了一种美妙的含蓄的诗歌氛围。中国诗歌理论还有一种比较基础的理论,就是所谓的“感物而动”,即上天赋予人的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等各种情感,由于受到外物的感召,而被激发活动起来,产生了文学创作的欲望和冲动,而文学的产生正是“感物而动”的结果。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感物而动是感物在前,心动在后,而感物伤怀则是伤怀在前,感物在后。而物却是伤怀所得以外化的一个载体,若无物,怀亦是不可发也。其所伤之事,多与个人身世有关,当他处于某个群体但是在这个群体之中却无法尽显才华,反而陷入了冲突之中,其结果往往是个人在此冲突之中感到无望,惆怅,因此而形成了感物伤怀诗(多为咏史讽今或者咏物伤怀之诗)。许多诗歌之中留露出了真挚,深沉的感情而且其中还有一股郁积于心中的郁郁不安,这种不安既是对个人的前途的不安,又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安。其间流露出的感情是惟有作为书生的知识分子方可生之,而肉食者们或起事者们的诗歌之中是均不会有此种气氛的,因为作为破坏者的他们的思维是简单的;而作为知识分子,却是对被破坏物有着一种同情而至于同感,因为它们自己认为自已担负着一种社会责任,但是同时却又不得为之,因此而将自己所有郁积之情抒发于眼前的景物之中,此景物乃此情的另一个载体。人于物相成的重点在于其能够抒发文人之怀,多是有抱负而不得志,有才能而不见用,而且受周围的险恶环境所戕害,因此必有一种惆怅在其中,从之感物而伤怀,其意不在物,乃是物之所可以发之怀而用之。
李商隐(约813 — 约858)是历代人们最喜欢的大诗人之一,他深沉而又神秘,严谨而又撒脱的诗风开辟了晚唐诗歌的另一个境界,是晚唐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著名的作曲家门德尔松(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二人的作品之中都洋溢着一种令人沉思的冥想。而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更是十分擅长利用身边的一草一木来表达内心的苦闷与抱负,他写的感物抒怀的诗歌有很多,也许大家对他的坎坷的一生并不了解,因此在分析他的作品之前有必要对他的身世作一下简要介绍: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迁居荥阳(今属河南)。少习骈文,游于幕府,又学道于济源玉阳山。开成年间进士及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宣宗朝先后入桂州、徐州、梓州幕府。复任盐铁推官。一生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备受排挤,潦倒终身。晚年闲居郑州,病逝。其诗多抨击时政,不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以律绝见长,意境深邃,富于文采,独具特色。为晚唐杰出诗人。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治争夺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令狐党人执政,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诗人有一部分咏物的名篇。他的咏物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且还处处都流露着对自己身世的感伤。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李商隐的咏物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所有诗歌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李商隐一生中写过许多的咏物诗,仅仅咏柳诗就有15首之多,有许多写得生动贴切,字字深情。
下面我将就一首名为《垂柳》的诗歌进行一下简要的分析: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
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
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
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
一,二句非常巧妙地写出了垂柳所在的地理位置,诗之中所咏的柳树在小苑中,在曲池东。曲池或者就是曲江,既曲江池,在唐代长安城东西,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李商隐作过《曲江》一首。此二句虽然是提出了垂柳所在的地理位置,但是此二句的妙处在于娉婷和婀娜二词,小苑和曲池说明柳树是在一个比较清高的环境之中,因此这也暗示了柳树本身的高贵和丽质,而娉婷和婀娜二词则说明了这一点,从全诗来看可以说这二词是在于说明柳树的特有动人而又娇嫩的形态。但是如果不看全诗,则这二个词还有着更加丰富的含义。唐朝的诗人有许多是以咏柳而著称的,娉婷和婀娜二词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了贺知章的一首诗歌中的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此句把柳树比作为小家碧玉,已经成为千古的名句,而李商隐的此二个词亦不减风骚,依然让人感觉到了柳树的阿娜多姿,宛如一个千金小姐立于此处,在此作者并没有象贺知章诗一样直接明显地利用小家碧玉来形容柳树,而是使用非常人性化的词语来形容一个植物,而且一.二句并没有提出柳树之名,因此很容易让人觉得在这里作者所描写的可能不是柳树而是人,由此可以推断出作者或许有意在给这里所描述的柳树以一种人格的东西,或许是把人的东西融合进了柳树之中,或许把柳树的东西放进人的身体之中,但是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无论柳树还是特定的人都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天生丽质,心灵手巧,或许这种品格在人的身上还有更多的才华的显现,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作者的早年时期,幼时随父到浙江。9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 (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诗人早年即有才,的到当朝官员的赏识,他身世的这写顺利的发展表现在了诗歌之中,在这两句诗中,我们甚至不仅仅能够看到才华出众,出口能成章的李商隐的影子,而且能够感到诗人的一些自恋,但是自恋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下面的诗句则一步步点明了为什么诗人在这前二句之中就对柳树大加赞扬,这也许会从下面的诗句之中得到答案。
三四句则写得更奇,“珮”指的是饰玉的珮带,以状垂柳,一作“佩”字,字通。我们可以感觉到此二句是接着一.二句写出来的,但是其内容并不于前两句相重合,而是更加进一步地描写柳是如何的端庄高贵,咋看上去,此二句仿佛是写人而不是在写柳,但是联系全诗却又觉得即便是写柳也是极其自然天成之语,无半点造作之意义,“朝佩皆垂地”言柳树的枝条皆垂于地上,以“朝佩皆垂地”更加人格化的方式来写这种情状,不仅仅是为了含蓄和深奥,更是在明写柳之中暗写了人。朝佩是指只有有地位又才能得到明主赏识的人才会戴的饰品,在此诗人为什么要用朝佩来形容柳树下垂的支条,一方面是因为二者的形似,但是其神似或许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以朝佩和和金衣来喻诗人自己的才华,而皆垂地,尽带风则暗示了诗人的才华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其间已经隐藏了一丝悲意。
五六句“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饶当让讲)中的七贤指的是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有:“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三品或曰为士大夫,白居易诗云“九龙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风飘管絃。”后人注释曰:“考少林寺有则天皇后封三品松,五品槐。”此二句所言乃指竹因七贤而多有风骨,而松则有武后将之与当朝名士联系而地位攀升。令人意外与费解的是,本诗通篇写的是柳,作者何以在此笔锋一转,似乎为意外之笔,所咏之物亦不再是竹了,仿佛有失于唐突。但是难道竹与松就一点联系也没有吗?那不尽然,所谓花之四君子,以松竹为首,以代指知识分子的风骨豪气,而此诗中所咏之物:垂柳在前四句作者已经赋予了它以娉婷婀娜之态,高贵脱俗之风,它的风度又何以低于松竹呢?七贤占竹,三品饶松,此突兀二句若不是另外含有深意,的确显地突然,清程梦然言:“五六句因柳而及于竹,柳不让竹,竹乃以七贤得名;又因柳而及于松,柳不让松,松且以三品骤贵,喻当时之得志者也。”可见以竹松来指当时得志之人,虽然表面上不是在写柳,却字字言柳,即便柳不让竹,即便柳不让松,但是竹有七贤所爱,而松有三品吹捧,惟有柳仅仅立于小苑曲池处,虽然雍容高贵,但却没有人会去欣赏。此句若细细去推敲,竟然可以发现作者深藏于其中的悲伤不遇之感,柳不见遇,还不是诗人自己不被重用的状况的写照吗?尽管当朝中人皆才华横溢,有能力辅佐君主,但是却忽视了诗人自己,前四句所言的所有的优点,也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惋惜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二句来得虽奇,却紧承前四句,看似毫无关系的垂柳和松竹,其实是垂柳两种不同境遇的对比。所谓感物抒怀有大小境界之分:小境界乃单纯以一物抒一情,此物此情互相交通,读者可以轻松地通过物读出诗人之情。然而此诗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大境界,虽为咏此物,中间却咏他物去了,读者只要细细一想,虽然表面上是在咏他物,可是实际上却是在咏此物也,而以他物代此物所抒发之情乃更切。在本诗中其实有两层的对比,一是垂柳本身与它所处的不相识的环境的对比,一是它所处的境地和松竹所处的境地的对比,如果不写松竹,恐怕后一层含意就显现不出来了。这也是本句写得奇的原因所在其实本诗中的前四句已经潜伏着一种悲伤的情调,因为四句均写了柳的正面的特征,仿佛让诗人感到了有一些自恋情节,而一物越是完美,就越容易和周围环境造成冲突,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一种悲剧性所在,而五六句则冲破了前面极度含蓄的暗示,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作者地位的凄凉,这不禁另人惊呼:为什么是这样,像你这样的人,难道没有天子会赏识你吗?难道天下没有一个皇帝是明君吗?这样一来,诗人已经完全获得了读者的共鸣。
因此作者顺理成章地写出了末二句,算是全诗的一个交代,也算是给读者的疑问的一个解答:“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本句是写柳还是写人已经不甚分明了,可以看作写柳,也可以看作写人。七句用了张绪的典故,《南史》云:“张绪年少有清望,吐纳风流,每期见,武帝目送之。刘俊之为益州,献蜀柳数竹,枝条甚长,状若丝缕,帝指于太昌灵和殿前,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甚爱如此”。末句的先皇,清朱鹤龄认为是文宗,此言不乏合理之处。说它写柳是因为七句的典故中的确有柳存在;说它写人,是因为在末句中出现了先皇,明显是在写诗人自己的身世。此二句写得极好,用典也很恰当,不看前文,悲意已出,一旦与前问联系起来看则悲情更甚,诗人所要表达的不遇之情读显现于纸上了,这是五六句引出的悲情的最终的显现,如果全诗仅仅写前四句,则不免让人觉得诗人是在顾影自怜,只写前七句,则好象是在嫉妒同人,一旦有了此二句则不仅仅言出了诗人感伤人世的原因,也间接指出了前面的“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是皆尽枉然,一个空字似乎以将诗人所有美好言词所承载着的欢乐和幸运一扫而空,在此仅着一个空字就可看出诗人的真实感受是何等的凄凉,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赋此诗,真正的用意是在“先皇玉座空”之句,言先皇已去,再也无赏识自己之人了,诗人的远大抱负也难以实现,而且纵览诗人的一生其宦途也一点不顺利,因此这也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哀叹。此时柳人已经合而为一了,所抒发之情已经达到了高潮,最后在一个令人惋惜而又境界坦荡的“空”字中平静地收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忧思。
李商隐的一生,受尽了封建黑暗势力的中伤、指摘和污蔑。他有“匡国”用世之心,热情敏感,秉性正直,爱憎分明,但由于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他受到压抑,无法脱颖而出,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万丈雄心归于幻灭。他对黑暗现实不能沉默,国家前途、人民生活不能采取漠然的态度,但客观的现实环境又不允许他大声疾呼、慷慨陈辞,宦官的淫威,党人的排摈,都给予他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另外还加上生活的重荷,也影响到他的感情。因此他就采取隐晦曲折、侧击旁敲的方式创作,运用比兴、象征、讽喻、双关、用典等手法,曲传不遇之恨,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他的诗歌就形成一种具有往复低回、一唱三叹,“寄托深而措辞婉”,意境幽微,隐晦曲折的朦胧之美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本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以前的人对本诗的分析或者说是喻他或者是喻己。但是喻他说显然与本诗的情调不合,从诗中潜藏的哀伤来看,借柳所欲言的只能是对诗人自己所发的。在此诗人自比垂柳,以写柳来写自己,以介绍柳的处境来言自己的处境,以感叹柳的身世来感叹自己的身世。作为借以抒发自己情怀的柳是李商隐笔下一个常常借用的一个道具,或许柳本身的气质就和诗人的情怀想契合,他还写有一些咏柳之诗:
柳
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
解有相思否,应无不舞时。
絮飞藏皓蝶,带弱露黄鹂。
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
巴江柳
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
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
赠柳
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
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
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
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
自感身世在所有诗歌之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追思文宗只有在本诗才是有的,这种对先皇的追念情节,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心中都是解不开的节,尤其是当诗人当前境遇不佳时这种情节就愈加明显。在古代诗人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者,或许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能否得到天子的赏识,委以重任,报效国家。李商隐历仕文武宣三朝,其中惟有文宗有知遇之感,史称文宗“自为诸王,深知两朝(指穆,敬二帝)之弊,及即位,励精图治”,力图挽回唐王朝江河日下之颓势,然而在位十四年,不仅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建树,而且使危机日渐深化,两次某诛宦官的失败,(一次为大和五年与宰相申锡谋诛宦官,事败,申锡贬死;另一次就是甘露之变),更足见其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努力无不事与愿违。图治无成,终于在“受制于家奴”的处境中去世。而作者一生仕途坎坷,多有羁绊,因此对文宗的追思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追思也是感叹人生与自己的命运。虽然如此,作者对文宗之思仍然有所寄托,因为在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的诸君主中,文宗仍旧是一个试图力挽狂澜的明主,他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与李商隐的身世有所暗合。因此作者以追思文宗来感伤自己也是很贴切的,这不仅仅是诗人对于先王的忠诚和敬仰,还是对先王身世的共鸣与同情,而只有身世相同的相似者才会有互相同情,这么看来全诗的感物抒怀之情就更加深沉了。
总的来说,诗中隐藏着的对照的确有很多很巧妙。以柳喻自己,以松竹喻当朝高士,又将先皇和自己进行对照,作者之怀不得不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但是主要说知遇之感还是伤悼之情呢?如果仅仅是知遇之感,那全诗也不会写得如此深沉凄伤,全诗除了末尾二句写知、遇之情外,其他其实都在写自己处境,而且这种处境导致诗人去怀念先王,因此伤悼身世才是诗人所要表达的重点。正如《庄严弥撒》(Missa Slemnis,Op.123,1822,Ludwig von Beethovon)虽然是作者写给长期资助自己的鲁道夫大公登基用的(以示知遇之感),但是本质上却是作者对自己一生创作和思想的总结。而在此诗之中,以柳来伤悼身世,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用柳既能表现出作者的性格,同样是平凡而不庸俗,高雅而不奢华,虽然仅仅是立于小苑却不减神仙之气,不被人们赏识却仍旧干直,不让与松竹,很能代表作者自己的胸怀远大,质朴真诚而又正直不阿的性格,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由柳之处境引至诗人之身世,由柳之“肠断灵和殿”而至于作者之“先皇玉座空”。诗人之性与垂柳之美相互融合,让人不仅仅感到一种美感而且还伤诗人之伤,不可不谓咏物诗的大境界。
注:
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以其善于用典著称的,全诗八句就用了四典故:竹林七贤的故事,则天皇后封松的故事,武帝怀张绪的故事,以及诗人对与文宗的思念,这些典故在诗中巧妙地与柳联系了起来,而且能够起到沟通柳和人事的作用。后世评家对李商隐的用典多颇有微辞,然而在此诗中虽用典故亦多,却看不出什么不和谐之处,他诗歌艺术上的这一个特性也是不能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