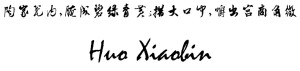最近遇到个案例,某外国公司对其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的商事买卖合同提供Comfort Letter,承诺在其子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赔偿对方的损失,且该Comfort Letter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并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还是诉讼。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做了一些研究。该案主要有三个问题:(1)在中国法下,该Comfort Letter是否构成担保法下的担保?(2)如果构成担保,该担保合同是否有效?(3)如果有效,是否可行?
(一)该Comfort Letter是否可以认定为保证合同?
该函件名为Comfort Letter, 即安慰函。关于什么是安慰函,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3103号)中,北京市高级法院认为安慰函通常是指政府或企业控股母公司为借款方融资而向贷款方出具的书面陈述文件,内容或者为表明对借款人清偿债务承担道义上的义务,或者为督促借款人清偿债务,或者为表示愿意帮助借款方还款等内容。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该安慰函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构成担保合同?实践中,问题函件会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出现,包括但不限于安慰函、承诺函等,特定的函件是否构成我国担保法上的担保,虽然在立法或者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判断一个文件的性质不是从其名称来判断,而是要从该文件所表述的具体内容、该文件达成的过程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
如果安慰函明确表示该函不构成担保,那么法院一般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根据“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3103号),如果出具的安慰函明确表示“本安慰函并非一种担保(中国国内及国外)”,那么,该《安慰函》就不是一种担保,出具方也没有愿意代为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
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该函不是担保,法院则会审核函件的具体内容,根据具体内容判定函件是否构成担保。
在“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上诉案”((2004)民四终字第5号)中,最高法在认定某函是否构成担保时,认为应当根据其内容来认定,并且确定出具某函的一方有承担保证责任或代所属企业还款的意思表示。该案中,佛山市政府向香港交行出具的《承诺函》中的“本政府愿意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履行还款责任,按时归还贵行贷款本息。如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贷款本息情况,本政府将负责解决,不使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并无明确的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人民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一案《承诺函》是否构成担保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27号)中,最高法也认为,《承诺函》是否构成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应根据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的背景情况、《承诺函》的内容以及查明的其他事实情况作出认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近的案例“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3号)中,最高法认为判定某承诺函的性质是否具有保证担保的性质,应当结合文本名称、出具背景、约定内容等事实综合认定。在本案中,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若该公司(指宜连公司)出现没有按时履行其到期债务等违反借款合同约定的行为,或者存在危及银行贷款本息偿付的情形,出于保护投资商利益,保障贵行信贷资金安全的目的,我局承诺按《特许合同》第15.6条之规定全额回购宜连高速公路经营权,以确保化解银行贷款风险,我局所支付款项均先归还贵行贷款本息”具有保证担保的性质,而非仅为道义上的安慰函。
综合以上案例,背后的逻辑是并不能因为函件的名称是安慰函,就否定其符合保证合同特征的可能性,所以对于某个特定的安慰函,仍旧需要从其内容出发,结合《担保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判定其是否符合保证合同的特征。
在该Comfort Letter中,有如下保证:“在M子公司无法履行和XX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M子公司因为破产或者运营困难导致的无法履行合同),M母公司保证将赔偿XX公司因M子公司的违约造成的损失和合理的费用。”(原文为英文)
该约定符合《担保法》第6条所规定的“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该Comfort Letter虽然名为安慰函,但是其内容明确约定在子公司不能履行主合同的情况下,母公司将赔偿债权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具有明确的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的意思表示,符合以上诸案件的逻辑,应当认定为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
(二)如果可以认定为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以上仅仅解决了函件的性质问题,即某安慰函是否构成担保,但是即便构成担保,仍旧需要解决该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简单来说,若担保合同符合《公司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且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该项担保合同在中国境内即有效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未经有效内部决议程序而向他人提供担保的,可能对担保的效力造成影响。
根据上述规定,在境外母公司为境内子公司的担保中,提供担保的境外公司也须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担保的内容、方式等事宜取得公司内部的有效审批和必要授权,以确保担保能够有效设立。
此外,《担保法》第13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 第15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一般而言,保证担保自合同签署时起生效。此外,根据《担保法》第9条的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
在“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3号)中,最高法虽然认定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出具的承诺函具有保证合同的性质,但是因为高管局作为湖南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事业单位,不得作为保证人。《承诺函》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
因为该Comfort Letter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其属于书面合同,且具体内容符合《担保法》第15条的规定,并且外国母公司并非《担保法》第9条所说的公益法人,故可以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
(三)如担保合同有效,其法律上可行性如何?
即便该Comfort Letter作为担保合同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且该合同明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是实际中其可行性也是一个问题。
1. 担保合同的涉外性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该担保合同的担保人是外国法人,所担保的资产在海外,担保若实施,是需要从一国交付到另一国。虽然该Comfort Letter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到了执行的阶段,依旧会涉及到担保人母国的法律和司法协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7规定,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该Comfort Letter没有说明发生争议通过诉讼还是仲裁手段解决,如果是诉讼,中国目前还没有参加1971年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或商事判决的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即便在中国法院胜诉,在执行环节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是仲裁,中国参与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M是一家外国公司,而本国也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仲裁裁决可通过中国的法院签发后向波兰的法院递送,在获得承认后,可以由本国的执行地法院协助执行。
2. 执行的难度
一旦发生担保纠纷,即使在中国的裁决得到母公司所在国的承认和执行,但是由于担保物资在国外,担保物的递送要通过境外一国或者第三国,不仅时间长、费用高、手续多,而且执行的难度和复杂度要远超在中国境内的执行。
所以,即便担保合同有效,而且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但是因为涉及到国外承认中国的判决或者仲裁结果以及执行,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难度。
综上所述,该Comfort Letter可以被认定为担保合同。如果该Comfort Letter符合该母公司出具担保合同的章程和其所在国法律的规定,那么因为该Comfort Letter的内容也符合《担保法》相关规定,所以该担保合同在法律上也有效。但是,即便如此,因为本Comfort Letter属涉外担保,且并未规定争议解决的方式,在后续的承认和执行的过程中,也有诸多的不确定性。